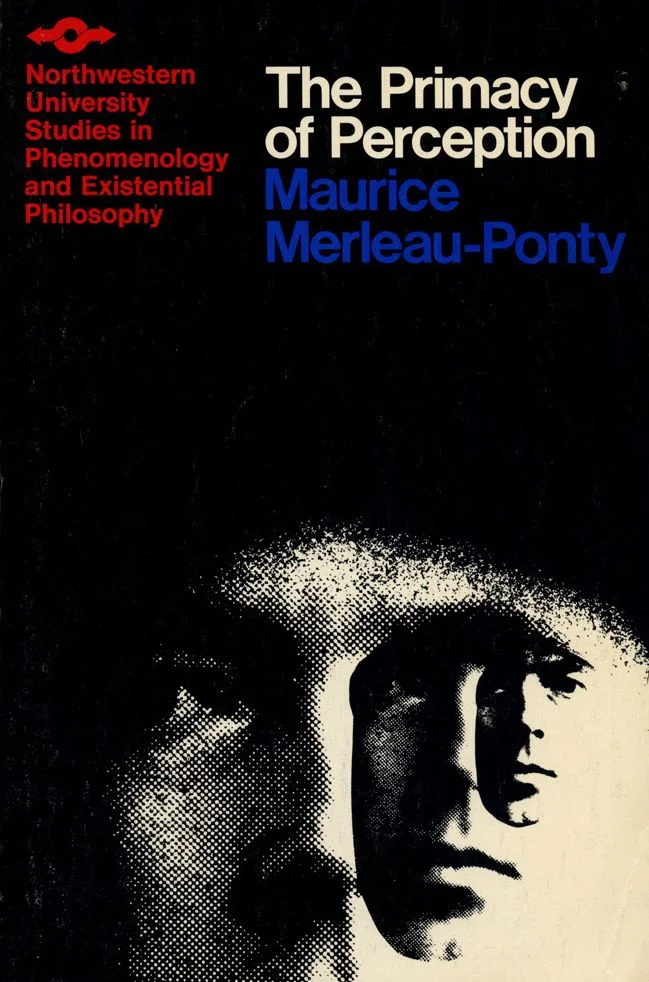《動亂》十四件「物」作為敘事者,重新定位對六七暴動的時候,不以人類作為中心決定政治取向,側重於人與物之間的物質性存有和互動。但是人非草木,到底劉氏又是否真的能夠做到人與物之間的平等? 還是只是把人的思維方式和視覺套到「物」的身上,以人類作為「物」的中心?
劉以鬯作品書影
文:凌志豪
香港文學巨人劉以鬯上月赫然離世,當然記得從前就讀中學時由劉先生的小說中取得許多啟發,是次希望以我在芝加哥大學交流一年的新見聞重看劉以鬯在《動亂》中的新小說實驗,特此紀念劉先生的實驗精神及創見。
劉以鬯自60年代末起受法國興起的「新小說」(nouveau roman)啟發,改變心理小說的手法,由注重內心的深層挖掘轉向結合表層人物動作描寫或景物描寫的手法。[1]《動亂》十四件「物」作為敘事者,重新定位對六七暴動的時候,不以人類作為中心決定政治取向,側重於人與物之間的物質性存有和互動。但是人非草木,到底劉氏又是否真的能夠做到人與物之間的平等? 還是只是把人的思維方式和視覺套到「物」的身上,以人類作為「物」的中心?
「新小說」的物導向面向
在討論劉以鬯如何移植新小說的技巧之前,我們可以先看法國新小說作家羅伯‧格里耶 (Robbe-Grillet) 提出的寫物理論,格里耶在〈自然本性、人本主義、悲劇〉(1958) 一文中提出了幾條具體的寫物原則: 其一, 拒絕隱喻與類比性詞彙; 其二,記錄物我的距離, 站在物的外部寫物,「描繪事物, 就是斷然地站到事物的外面,去直面它們。它不再是把它們擁為己有,也不是帶給它們一些什麼」; 其三,消解意義,削平深度,描寫事物的平面。[2] 在新小說之中,人與物,人與世界的相互關係被重新界定,物是獨立於人物而不從屬的存在,新小說肯定了兩者之間的距離。拒絕隱喻和強調物我距離都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撥,不再將物件作為隱喻心理的工具,僅僅作為人類的投射,而承認其外在於人的獨立性和不為人的文學語言所把握的不透明性。
回看劉以鬯的《動亂》,跟從格里耶的原則,記錄物我的距離,寫出了人與物的距離,不論是在動亂中被作為工具而後棄置的催淚彈、刀、汽水瓶、水喉鐵,還是無端遭受損毀的郵筒、垃圾箱、計程車,抑或只是冷眼旁觀的街燈與電車,每一物件的敘述都強調物與人兩個世界的無法溝通,對事件成因或何以身受其害,皆言「我不知道」、「無法了解」、「我死得不明不白」,又例如電車說:「我不知道為甚麼要在此犧牲。這裏邊應該有個理由。我不知道。」、垃圾箱說「我不知道他們為甚麼這樣恨我」。劉以鬯把「物」的世界與人的政治分割,兩個世界存在著截然不同的邏輯和觀念,無法互相理解,物質上已者存在著同一個空間,但卻有著必然的距離,一段無法接近的關係。
「物」的世界意識形態上獨立於人的政治事件,有著一套截然不同的邏輯,例如電車,即使當「有人用鏹水向我擲來,灼傷了兩位乘客,迫使他們從車廂裏跳出。」、「司機也被人用石頭擊中額角,流出很多血。」等觸目驚心的血腥場面,也只覺得「我只有好奇,一點也不緊張。」, 看見群眾因「疾步散開」催淚彈,對電車來說「氣氛相當緊張。我倒覺得有趣。」,因為對於電車「這是新鮮的經驗。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電車因為它無法感受人類流血的痛楚,所以無法把同理心投射到人類身上,「物」的世界與人存有的物質條件不同,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構模式不能夠直接套用到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之上。相對而言,劉以鬯嘗試以人的角度設想物與物之間的關係,當電車看到「我看到吃角子老虎被人用鐵棍打彎了腰;我看到一輛計程車正在燃燒。」能有設身處地的想像,感受到對方的痛苦,故有「我是比較幸運的。」的心態。
「物」的世界與人的世界觀念上的不同還可以從刀的例子中看出來,小說刀雖然被用來殺死一位青年,但刀只是把物理性的關係客觀地呈現出來: 「一個青年將我插在另一個青年的腰部」、「我在血液中沐浴」。刀與被殺青年之間不存在道德判斷,人的倫常並不適用於「物」之上,刀於此處只是謀殺行為操演的工具,「物」本身並不帶著殺意。劉以鬯擺脫人類中心的思維,從物的角度消解六七暴動的政治意義,削平深度,描寫事物的平面,注重物理結果。
六七暴動的資料圖片(來源:網絡)
「物」的兩種形式
物為導向的本體論創始人格瑞漢姆·哈曼(Graham Harman)一將物區分為擁有不同「質」(quality)的各種類型,在他的著作「四重的物」(The Quadruple Object,2011)中指出:「儘管宇宙中也許存在無窮多的物,但它們其實只有兩種:一種是與任何體驗無關的真正的物(real object),另一種是僅存於於經驗中的感官的物(sensual object)。於是相應的,我們也擁有兩種質:一種是存於經驗中的感官質(sensual qualities),另一種是胡塞爾所說的只能通過理性而非感官本能才能接觸到的真正的質(real qualities)。」
劉以鬯在《動亂》中也呈現了兩種物的狀態,對「物」的物理性破壞和消逝及觀察暴動的方式劉以鬯用擬人的經驗呈現,用上「受傷」或「重傷」來形容各種物件被破壞的情況。又例如,吃角子老虎吃角子也用上人進食「食糧」的比喻,被人「用鐵棍打我,直到我彎了腰」,將吃角子老虎的身體幻化為人類的身體。對於各種物件物理狀況的擬人化比喻建立在人類經驗中的感官質(sensual qualities)的基礎之上,故此這是感官的物(sensual object)。相對而言,上文提及到的「物」的世界與人世界的距離,截然不同的觀念和邏輯,則是由物和人之間物質性差異所推論出來的設想,是理性思維非根據感官經驗的推敲,是故為以理性而非感官本能的真正的質(real qualities)接觸到的真正的物(real object)。
"The Quadruple Object"書影
物與非物之間: 一種曖昧主體
無論是哪一種物件《動亂》中都反覆地「看見」動亂的視域(vision),視域亦是主體構成的過程。梅洛﹣龐蒂曾指出:
「視域不是一種特定的思想,或面向自我的在場(presence)。它賦予我一種中介,讓我抽離自身,但同時由自身內部(而不是存有的面前)處身於存有(Being)的裂縫(fission)中,這個裂縫的終站,正是我回到自己之處。」[3]
劉以鬯通過將「我」變成「物」的敘述者,一方面在閱讀「物」,另一方面以人的身份成為了「物」,身份介乎於二者之間,視乎讀者如何接收。這樣令他抽離了人類中心的世界,令自己身處裂縫之中,重新審視這一場暴動中對他來說最核心的經驗。每一件「物」雖置身這場動亂中,但卻多次強調「我」「我不知道」、「無法了解」、我的不明所以,表明了在觀念上和意識形態上並沒有參與暴動的意識,「物」的物理條件限制也使劉氏無法作出行動,只能身不由己的被破壞,設下了一種對「六七暴動」旁觀者的視角及關係,而且這個非人非物的旁觀者並沒有站在反對和支持的對立面上,而是一個曖昧的位置。例如最後一段「我」 變成了一具屍體:
「我是一具屍體。雖然腰部仍有鮮血流出;我已失去生命。我根本不知道將我刺死的人是誰;更不知道他為甚麼將我刺死。也許他是我的仇人。也許他認錯人了。也許他想藉此獲得宣洩。也許他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總之,我已死了。我死得不明不白,不若螞蟻在街邊被人踩死。這是一個混亂的世界。這個世界的將來,會不會全部被沒有生命的東西佔領?」
雖然被殺死了,重點似乎並不在於被殺死的憤恨,或者對失去生命的失落,而是從人的身份化為「物」,重申「我」對一切不知,不知誰是兇手,不知動機,是「不明不白」的。跟人類世界的政治意識形態鬥爭分割開來,以人與「物」的鴻溝,建構一種架空與政治事件上的主體,然而這個主體係存在與否,是否介乎於「物」與人之間,一切我們都沒法確切判定,只能在一種「不明不白」的曖昧中尋索。也許這也是一種香港的視角,在二者之間抗拒及浮游,或許在形成 (becoming) 的路上。
真正佔領著這個世界的可能不是人類而是「物」,我們創造了「物」嗎? 但所有「物」不是由其他「物」組成嗎? 創造的過程是我們在「物」身上施展我們的動能 (agency) 還是「物」的動能在引導我們? 不論「這個世界的將來,會不會全部被沒有生命的東西佔領?」,我們都一步步在跨越人與物之間的鴻溝,生命慢慢在流逝,將來必然成為無生命的「我」,無生命的「物」。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書影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文學院學生,主修藝術及比較文學、香港大學Cultural Leadership Youth Academy成員、Association for Asian Performance會員。曾獲青年文學獎、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藝術同行2014最佳表現獎等。
[1] 黃勁輝: 《主題活動試閱劉以鬯與香港摩登:文學‧電影‧紀錄片》, 香港:中華, 2017年, 第150頁
[2] 羅伯‧格里耶:〈自然本性、人本主義、悲劇〉,《快照集為了一種新小說》,
佘中先譯,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第119-140頁
[3]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4. "Eyes and Mind."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159-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