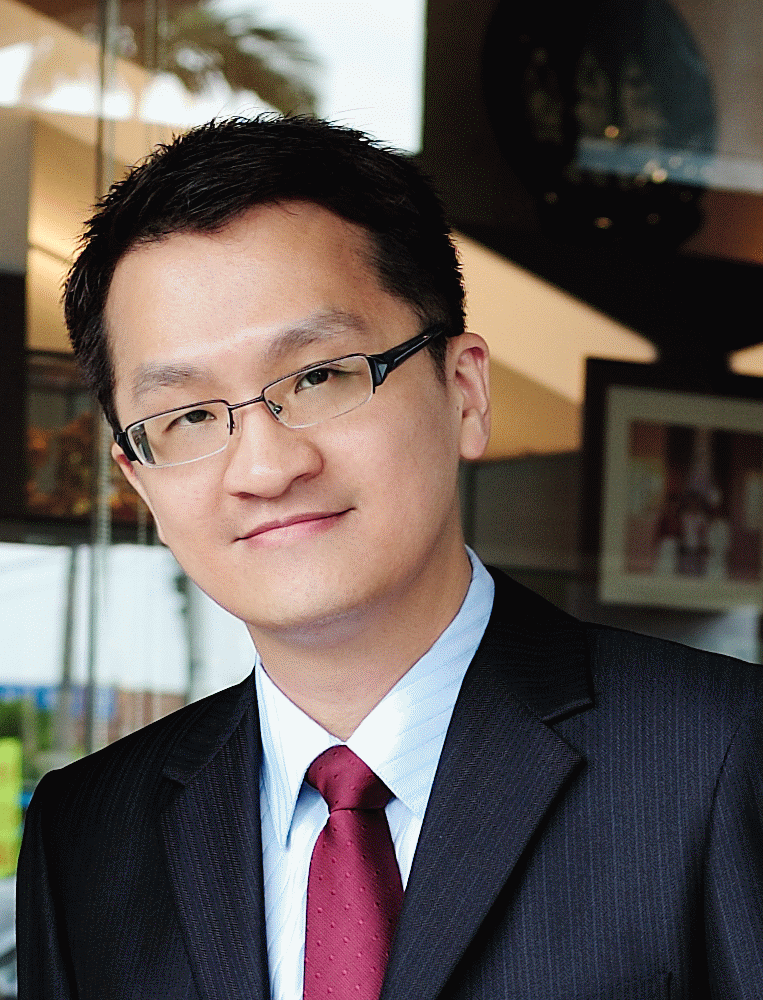「文字傷舞」,兩種媒介似是南轅北轍,但作者卻從中看出不同藝術媒介有其共生性與放射性。文學的價值正正在於它的可塑性,可以在其它媒介中找到共生的可能。
《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書影
(相片及文章均由作者授權轉載)
文/區仲桃
「見自己,知天地,愛眾生」──吳美筠在《獨眼讀看──劇場、舞影、文學跨世紀》的序中借用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裏的對白,道出了自己近三十年來藝術評論文章風格的轉化過程。也許我們可以進一步演繹這句對白,嘗試用來概括這部評論集的內容──它是對文學(自己),對文學和其它媒體(天地),對文學與社會大眾(眾生)等種種的一種審視。
書中<感冒誌>劇照,拍攝:張志偉 & Keith Sin@Hiro Graphics
文學到底是什麼?對於這個老掉牙的問題,吳美筠並沒有用尋常的方式來解答。狹義來說,四十五篇藝術評論文章中,直接寫文學作品的只有評羅少文的詩〈獨行的太陽成絶響〉、董啟章的小說〈扭曲人與港產物我與文學的相生鏈〉及楊絳的散文〈楊絳:把散文變成夢里長夢〉這幾篇。作者用更多的篇幅探討文學與其他媒體的關係,特別是當文學轉化成其它媒介時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其中包括文學與劇場、舞蹈及電影中問的媒體轉換。把觀眾熟悉的文學作品例如《雷雨》、《離騷》等改篇成為舞蹈時,吳美筠認為很容易讓觀眾失望。加上「文字傷舞」,兩種媒介似是南轅北轍,但作者卻從中看出不同藝術媒介有其共生性與放射性。文學的價值正正在於它的可塑性,可以在其它媒介中找到共生的可能。吳美筠在評論劇場版《感冒誌》時點出:劇場版「捕獲和傳遞的不是語言表面的內容,而是關心難於把握、不可解的部分。」這裏指的神秘和不可解的部分,作者在評論《帝女花》、《美的葬禮》時寫得更明白透切,那是指抒情及詩意。吳美筠借高行健在電影《美的葬禮》裏的話說明:「在商品拜物教和政治無孔不人的時代,竭力尋找喪失了的美和詩意。」在唐滌生的《帝女花》中,吳美筠進一步讀出劇中亂世駙馬的情意──「面對無邊的政治重壓,也不輕言放棄」,她認為這份情正是「香港土產經典戲曲劃時代的文學性」。
動藝改編<離騷>的舞蹈演出(圖片來源:舞團網站)
吳美筠也藉著書評表達了她對文學與社會大眾的看法。其中借《詩性正義──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思考雨傘運動,她提出了目前社會運動的公眾話語缺乏公正性,各種討論基於不同群體的利益,各為其主。她認同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提出的「公眾話語的公正性,必須通過文學所呈現的暢想(fancy)和敘事想像(narrative imagination),而這兩項恰恰是民主社會必然需要的組成部分。」最後,我們也許可以同樣以王家衛電影的對白,為吳美筠的評論集的成果作一個小結,它讓讀者們見文學,見香港,見眾生。
《 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 》書影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香港教育大學助理教授。曾任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包括現當代中國文學、比較文學及文化研究,及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等。









![[清]張竹坡批評 皋鹤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一百回 清康熙年影松軒刊本殘卷圖片來源:網上資料](https://images.squarespace-cdn.com/content/v1/5ab87b275417fc5a89522b70/1535907526365-3SJ34AMEPHF0QTS62AY7/%E5%BC%B5%E7%AB%B9%E5%9D%A1%E7%9A%8B%E9%B6%B4%E5%A0%82%E6%89%B9%E8%A9%95%E7%AC%AC%E4%B8%80%E5%A5%87%E6%9B%B8%EF%BC%9A%E9%87%91%E7%93%B6%E6%A2%85_%E6%9B%B8%E5%BD%B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