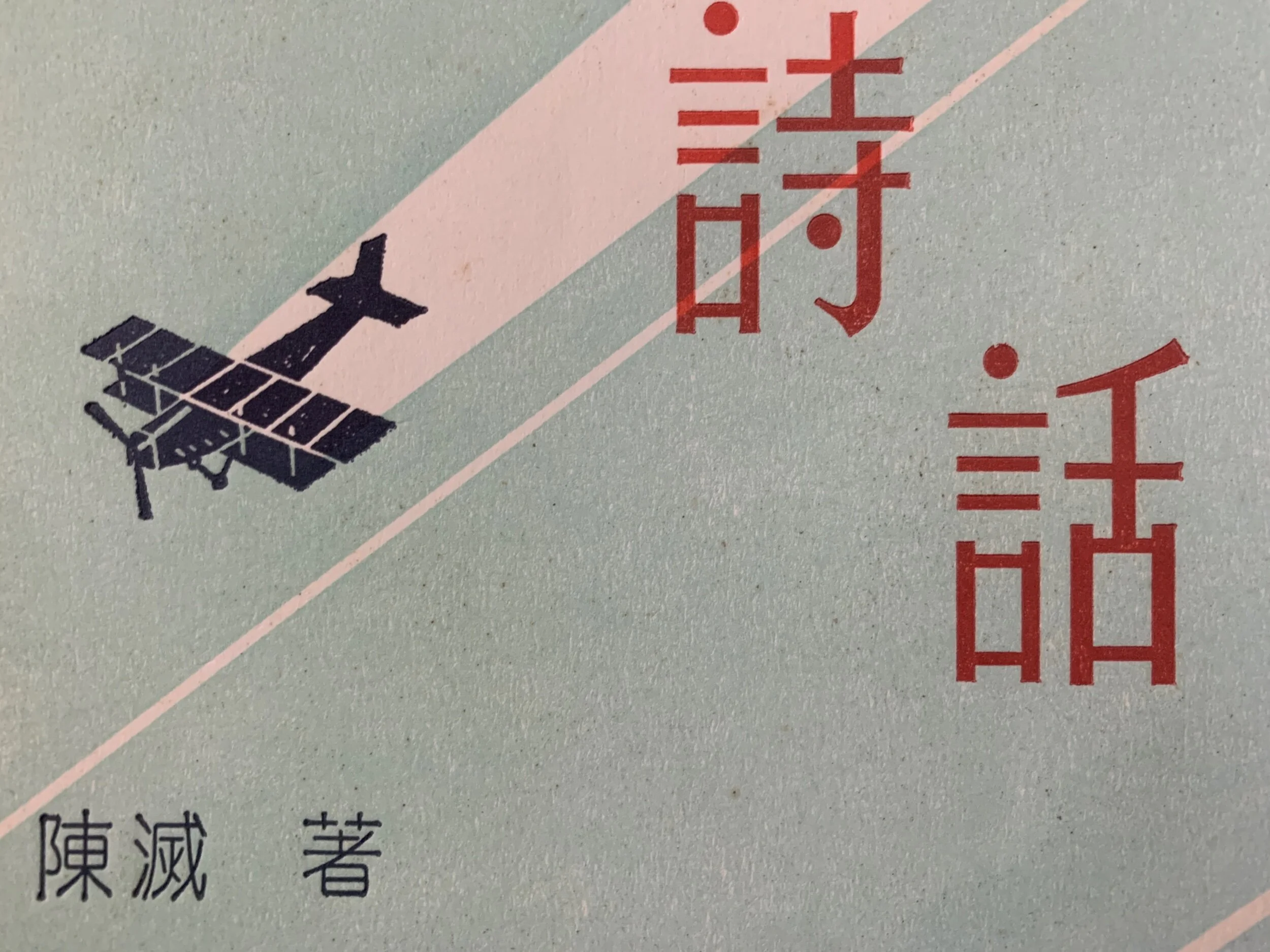藝術源於生活,生活造就了藝術;公屋生活孕育了「公屋詩」,詩人以不同的切入點寫公屋故事,也就展現不同的公屋生活面貌和藝術風格。
文/陳永康
舊型公屋景點多
跟所有城市的發展軌跡一樣,住屋問題是香港人生活的頭號問題,這也同時成為了詩人筆下的寫作題材,孕育了許多「房子詩」。在眾多以房子為題材的詩作當中,又以「公屋詩」最為豐富。此類詩反映公屋居民的生活,是香港普羅市民的集體情懷。讓我讀讀鄧阿藍早年寫的公屋詩〈舊型公屋〉:
〈舊型公屋〉沒有分節,一口氣記敘、描述舊型公屋的各種面貌,此詩行文簡單易明,「詩路」亦恰若詩末那群外籍遊客的遊踪,讀詩如隨遊客「興奮地舉起相機/帶著懷舊的遊興/在匆匆的行程中/拍攝徙置大廈的照片」。不同的是,「照片」只能記敘色相,「詩」則聲色俱備:
我們且隨「風」從舊型公屋「住戶合用的入口」進去參觀、拍照,又隨風「流去舊型屋的大門」,結束「匆匆的行程」。「行色匆匆」是因為景點多,行程豐富,還是舊型公屋聲色味難耐,誰願意久留?
流口水孩子的成長秘密
鄧阿藍的〈舊型公屋〉如流水賬般交代公屋的整體面貌,黃茂林則要領我們去看一個「流口水的孩子」;一個屋邨孩子成長的故事:
黃茂林的〈屋邨孩子〉寫「流口水的孩子」在屋邨成長的故事。「流口水的孩子/高高站在窗口/他俯瞰天空和大地」,「這孩子長得真快/卻沒有人稱讚他聰明」、「卻沒有人够敢提起聰明」──那是一個弱智孩子的成長故事,屋邨狹窄的居住環境原來包含我們無法逃避的教育問題。到底有幾多「流口水的孩子」的「成長秘密」我們視而不見?有幾多孩子撕掉大人送的《格林童話》?應該如何將「愛」獻給孩子,而不是僅僅給他們一個住所?這是詩人關心的問題。
黃茂林的〈屋邨孩子〉不光寫一個弱智孩子在屋邨的成長故事。詩中反覆吟詠孩子「俯瞰天空和大地」,說他「長得真快」,卻從不「讚他聰明」,不會「提起聰明」無疑是「流口水的孩子」發出的哀號和控訴。然而,就連一個「流口水的孩子」,看見「跌到樓下」的動物,都懂得「快速奔跑下樓/找躺臥的野獸,找受傷的野獸」,「說要領養回家/說要縫針,說要換血/流口水的孩子不曾掉淚」。詩人最後總結「他也有愛的秘密」,嘎然而止。這不由得我們心頭一震:有哪些「愛的秘密」我們忽視了?在香港,普羅大眾居住的屋邨裏有幾多「流口水的孩子」的「成長的秘密」需「要縫針」、「要換血」?
吃「媽咪麵」的「屋邨仔」
黃茂林的〈屋邨孩子〉給我們揭開孩子在屋邨成長的教育問題。不過,洛謀的〈屋邨仔〉似乎向我們給出了屋邨孩子的「成長秘密」:
洛謀的〈屋邨仔〉記敘「屋邨仔」在政府屋邨成長的生活片段,也是不少香港勞苦大眾的童年縮影。「屋邨仔」雖然有書讀,卻自小要學會照顧自己:
屋邨仔背著書包
在樓下士多買包媽咪麵
吃「媽咪麵」的「屋邨仔」原來沒有媽咪為自己做午餐。除了吃,「屋邨仔」也會安排自己的課外活動:
在屋企食完麵
攤在床上睇下季節又似人生
之後問阿爺攞五蚊
背起書包就落小童群益會
香港的「小童群益會」致力照顧被家庭忽略的兒童,讓許多無所事事流連街頭的街童重拾正軌,是青少年學習、娛樂的好去處。「屋邨仔」:
有時不去小童群益會
屋邨仔會去找七樓的同學
上來教他踩單車
同學推單車的後面
屋邨仔從走廊頭踩到走廊尾
停一停挨著圍欄看飛機
「屋邨仔」家住狹窄的屋邨,在「昏黃的走廊」踩單車,「閃避阿禾踩滑板」,「一個失平衡踩爛咗劉師奶個香爐」,然後「搬埋單車落十樓再踩過」。在惡劣環境成長的「屋邨仔」貧亦樂。
「屋邨仔」還要面對品流複雜的鄰居:「架車立又有人屙尿」,「樓梯口噴住紅色字/叫某某人還錢/之前那裏用黑筆寫住水房」。可幸那都是大人的事,「屋邨仔」不會做壞事:
當然會去下辦館
換一堆五毫子
在舖頭後面彈下波子
贏咗,咪買包薯片食囉
洛謀的〈屋邨仔〉往往口語入詩,親切的語言訴說親切的故事。一個知足自愛,自得其樂的「屋邨仔」躍然紙上。
牆上的可口可樂
「秘密成長」的「屋邨仔」終有一天長大成人,簡陋的屋邨也有老去的一天。為了滿足日益膨漲的住屋需求,重建舊型屋邨讓城市塵土飛揚,也同時留下唏噓和傷感:
鄭政恆的〈公屋〉寫舊區重建,舊型公屋人去樓空,空餘「平面的」、「空的」事物。這裏「不能喝」,只有「鏽蝕啃咬鋼鐵的手肢」,是一個「缺少空氣」、「缺少水份」的廢墟。舊公屋「在鐵絲網中沉吟」,「十三天後平地廢墟上升起了一縷白煙」舊居倒下,「拆毁了的房子並不會原地復原」,人們從此不再相信貼在門上的「出入平安」、「天官賜福」。
〈公屋〉挑了幾個屋邨居民最熟悉的意象追悼即將逝去的家園:「牆上的可口可樂」、「雜貨店旁邊的雪碧」是大家熟悉的廣告;茶餐廳的「鷹牌煉奶」和「奶茶」是生活的記憶;夏日裏機器聲隆隆的「冷氣機」、「抽風機」和「水龍頭」的哇啦哇啦是不可缺少的「空氣」和「水份」。這些事物還得有那「一雙手的撫觸」,才是「立體」的、永恒的。「你並不相信」拆卸了的舊屋邨「會原地復原」。
「鄭政恆的《公屋》寫年華老去、行將拆卸的公共屋邨,從前的生活場所變成了平面的汽水廣告,因為人的痕跡都消失了,「穿上綠色的絲網就不再寒冷了/十三天後平地廢墟上升起了一縷白煙」,是近日處處舊區重建的寫照,非人化的城市變遷比什麼都要超現實。」(葉輝評語)
大白田街的新型公屋
「舊型公屋」變成了「一縷白煙」」,且再讓黃茂林出場,領我們去八、九十年代雨後春筍般聳立的「新型公屋」看看:
黃茂林的〈大白田街的斜坡〉寫遷居「公屋」的感受,詩甫開首就向我們交代了新的居住環境:「六月份才搬進石籬二邨」/靠山的那頭/就是青巒接連的安蔭邨/這位置已瞧不見」。
詩人在第二、三節倒敘交代了這新居「已瞧不見」「青巒接連的安蔭邨」的來龍去脈。那該由去年年底前說起吧:「房屋署的主任說/你符合了居住條件,請簽名」。於是,「年底我們花了一大筆錢裝修/夏季把所有人口與雜物一天內送來」。新居入伙,「日子叫人鎮定又無奈」……
「鎮定」是「房屋署的主任說/你符合了居住條件,請簽名」,終於在這個地少人多,房價高漲的城市裏,覓得一個安身之所,入住政府資助的「公屋」;「鎮定」還因為新居「離街市近了一大步」,生活方便了許多,且「窗戶朝南」,可以吸收清新空氣……
「無奈」是擠迫的居住環境,「二房一廳,再次塞滿了人」。窗外還「多了一個地盤(建築工地)」。原來朝南的窗戶,「距離山的感覺似乎又遠了」,「青巒接連的安蔭邨」,轉眼「已瞧不見」。想起「山與水,在合同中也沒有註腳」,既然心甘情願搬進「石籬」,自然瞧不見「安蔭」。一語雙關的屋邨名稱,讓「無奈」增添幾分幽默。
詩的第四節正式入題,直接寫「大白田街的斜坡」。我們沿著詩人前面三節的鋪墊,讀到「六月份才搬進石籬二邨」的新居,「已瞧不見」山的青蔥、讀到「青巒接連的安蔭邨」,「距離山的感覺」日遠。如今憑窗放眼所見「大自然」的景象,就只有這個斜坡,那是「你」唯一「接觸到的斜坡」,卻「停滿了卸貨的車輛」。此時,陽光「溜過發亮的鋁窗外殼」,「一群孩童從幼稚園離散/小小的生命/悄悄沿著斜坡/銜接山上傳來的清涼空氣」。全詩給讀者留下一個富有寓意的畫面作結。
來自天水圍的公屋系列
由鄧阿藍的〈舊型公屋〉到黃茂林〈大白田街的斜坡〉的「新型公屋」,我們隨一眾詩人見證了香港人的公屋生活點滴;「公屋詩」也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走到今天。新世紀寫「公屋詩」寫得最多的可能是周漢輝,詩人自2015至2017年間完成了他的「公屋詩系」共十三首詩。讓我們來讀讀打頭炮的這一首:
周漢輝的〈暫時的河〉記敘「你」「隨某朵雲/走過了輕鐵車軌」,走過「小山」、「曲徑」,「爬抵峰頂」,過「橋」行「山徑」;「你」走過「天澤天恩天華/諸邨沿渠交替像昨天與今天」,待到「你駐足時/天地變暗」。然後「盤旋,雨彈,甩打,羽身」,「你」全身濕透。此時「水漲過泥窪,淹造暫時的河」,你「走入雨後,晴光照水」沐浴在「暫時的河」……
「你」孤單的走自己的路、自己的人生,「粤語/和普通話避開你,狗吠停你」。「鳥影比你略寬,孤單劃地/你只聽得風聲,後來水也低唱/天水圍人的故事在腳下淌流——」。「你」的故事也一樣孤獨地流走……
「你」窮困,「你」走(活)了大半生,「就此半生,至今/回頭雲朵散消,留下腐臭/吸引你尚留在地上。水流/依時收退,恢復渠貌,淤泥/垃圾,必有你多年所撒所拉/跟你腳步行進」。跟許多同道者一樣,「二胡獨奏,還是歌唱於口琴」,「當音樂休止」,大家都走到一起,「認得彼此,在勞工處/在社會福利署」,以為山窮水盡,「你跨越渠欄。卻止住。」「你」要繼續走下去,像「俯衝掠食」的水鳥,要懂得把握這「暫時的河」、暫時的生機……
周漢輝的〈暫時的河〉內容豐富卻不好讀,「幾近碎片化了」(羅樂敏評語)的敘事方式,讓人摸不著頭腦。此詩以公屋為名,卻不寫公屋,而寫公屋旁邊的一條小河;寫河畔公屋居民「碎片化了」的故事。詩人就明言此詩「只寫人的動態,同時覺得把敘事徘徊於僅僅可見的表層已有足夠的力度」(〈暫時的河〉後記)。不過,發掘碎片背後的故事有助我們更好的理解此詩的內涵:
〈暫時的河〉取材自天水圍「天澤天恩天華」諸公屋旁邊,一條通往深圳灣、後海灣的明渠(小河)。明渠每當下游的後海灣漲潮或者退潮的時候,便變成了「暫時的河」,正是水鳥捕食的時候。「暫時的河」在冬季充滿生機,小河聚集了北方飛來的候鳥在覓食。也同時也引來不少「龍友」「支架上照相機/鏡頭把人眼長長拉進/向水邊泥窪,陷凸陷凸/許多呼吸——它剛失去影子」,攝影機在忙於捕捉水鳥捕食的影子。
「天澤天恩天華/諸邨沿渠交替」,河岸邊常聚集退休或者失業人士,總有人在「二胡獨奏,還是歌唱於口琴」。明渠岸邊也有「天光墟」,每天清晨附近居民都愛聚在這裏做買賣,中午前便散去。那是天水圍居民的一條「暫時的河」──一條生活的河。不過,也因為這條「暫時的河」,有人丟了性命。2006年一名小販因為逃避食環署小販管理隊追捕而跳河,不幸給明渠溺斃。「對岸那人逃跑中,丟了大布包/草藥混雜零錢,三個制服人員/窮追上去,又像你止住。一隻手/既舉破水流,沉沒處有魚跳起/涉水間,放大,供它俯衝掠食」。「暫時的河」變成了「它俯衝掠食」的河。
〈暫時的河〉碎片背後包含激動人心的故事。
小結:公屋詩的遠與近
藝術源於生活,生活造就了藝術;公屋生活孕育了「公屋詩」,詩人以不同的切入點寫公屋故事,也就展現不同的公屋生活面貌和藝術風格。
鄧阿藍的〈舊型公屋〉如實反映早年基層市民在公屋的生活情況,詩人將舊型公屋的「日常聲色」雜然前陳,簡單直接。淺白易懂的語言是普羅公屋居民質樸的文風。我們便由「風」引領,「經過」、「進入」居民的生活,聽他們「訴說」公屋的生活日常。〈舊型公屋〉全詩句句是對惡劣居住環境的直接控訴;是一首舊型公屋居民的哀歌,這與詩末外籍遊客「興奮地舉起相機/帶著懷舊的遊興」形成強烈的對比。
相對於鄧阿藍的激憤,鄭政恆的〈公屋〉則著意製造冰冷、虛無乃至荒謬。詩人刻意強調本來就是「平面的」廣告牌、揮春「是平面的」,將大家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宣傳和祝願本來就與具體事實無關,從來沒有理所當然的事物,你熟悉的生活跟舊日的公屋一起,瞬間化作「一縷白煙」。「世上有太多稀奇的事情」,一切都在你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已然發生,詩文也在「你不相信」、「你並不相信」的錯愕之中結束。
黃茂林的〈屋邨孩子〉和洛謀的〈屋邨仔〉不謀而合,都寫屋邨孩子的成長故事。洛謀聚焦「屋邨仔」每天放學後的生活日常,從「屋邨仔」的語言、生活出發,親切、真摯的行文,盡顯「屋邨仔」自得其樂的童真。黃茂林挑了一個「流口水的孩子」來寫,卻推而廣之,向我們提出了「愛」「如何呈獻給孩子」的教育問題。詩人巧妙地將對「屋邨孩子」發出的同情哀號,轉變成「愛的秘密」──對教育的反省。
「公屋詩」由「近」及「遠」;由「住所」,走向「社會」還見諸黃茂林的〈大白田街的斜坡〉。〈大白田街的斜坡〉寫入住公屋的無奈,詩人一方面慶幸能入住公屋,一家人總算有一個容身之所;另一方面又有感於都市成長的新一代「小小的生命」,就在不斷聳立的石屎森林裏、在「鋁窗外殼」旁邊「銜接」斜坡上遠山傳來的空氣和陽光。我們由沒有房屋居住到公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城市建設佔去了原有的「空氣和陽光」,「停滿了卸貨的車輛」的「大白田街的斜坡」成了發展與安居的矛盾象徵。〈大白田街的斜坡〉花大篇幅描述遷居的矛盾心情,與詩末不露聲色的點題安排,加強了這種矛盾心情的無奈感。
如果說黃茂林的「房子詩」已經不再著眼於「房子」,那麼,周漢輝的「公屋詩系」就走得更遠。〈暫時的河〉寫的是天水圍公屋旁邊的一條明渠;一條不知名的小河──「暫時的河」是附近公屋居民的寫照。此詩也技出驚人,全詩由敘述「你仰隨某朵雲/走過了輕鐵車軌」開始,我們便隨主角走,卻發現很難走下去。那些「碎片化了」(羅樂敏語)的意象、情節讓人迷失。詩人彷彿陷入了自說自話的漩渦──那是只有天水圍居民才知道的故事。詩人在回應此詩作法時就不諱言:「寫詩過程不外乎一次次剝離與捨棄,詩中人物的背景在在留於我腦袋裡,而沒有下到筆端,突然對交代與解釋厭煩起來,只寫人的動態,同時覺得把敘事徘徊於僅僅可見的表層已有足夠的力度。」(〈暫時的河〉後記)對於這種寫作的自信,或者任性,詩人是自覺的:「公屋詩系在我的任性下告一段落……詩題〈橙路〉無疑也來自任性……」(周漢輝臉書「香港公屋詩系」〈橙路〉後記),周漢輝在回顧「公屋詩系」的創作歷程時就明言:「打從第十首〈橙路〉開始,筆觸偏離外在的公屋環境」(周漢輝臉書「香港公屋詩系」〈柏德小學〉後記)。事實上,對比周漢輝早年收錄在《長鏡頭》(波希米亞《長鏡頭》風雅出版社 2010年8月15日)的「公屋詩」,不難發覺「公屋詩系」無論內容和作法,都是詩人意求變的結果。我們也樂意看見自信的詩人,詩路上從此走得更遠、更放、更任性。
註:
鄧阿藍,〈舊型公屋〉,《一首低沉的民歌》 呼吸詩社 1998年11月。
黃茂林,〈屋邨孩子〉,《秋螢》復活號第十二期,秋螢詩社,2004年6月15日。
洛謀,〈屋邨仔〉,《島嶼之北》文化工房出版,2010年7月。
鄭政恆,〈公屋〉,《秋螢》復活號第七十期,秋螢詩社,2009年4月15日。
黃茂林,〈大白田街的斜坡〉,《魚化石》麥穗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
周漢輝,〈暫時的河〉,周漢輝臉書「香港公屋詩系」,2019年3月讀取。
(按:題目及分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簡介:陳永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現職中學教師。詩、文散見於《香港文學》、《文學世紀》、《秋螢》詩刊、《詩潮》詩刊、《聲韻詩刊》、《大頭菜文藝月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香港詩選2011》、《香港詩選2012》、《香港詩選2013》、《香港詩選2014》等。撰有《新詩讀寫基本法》、《新詩賞析基本法》、《愛情詩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