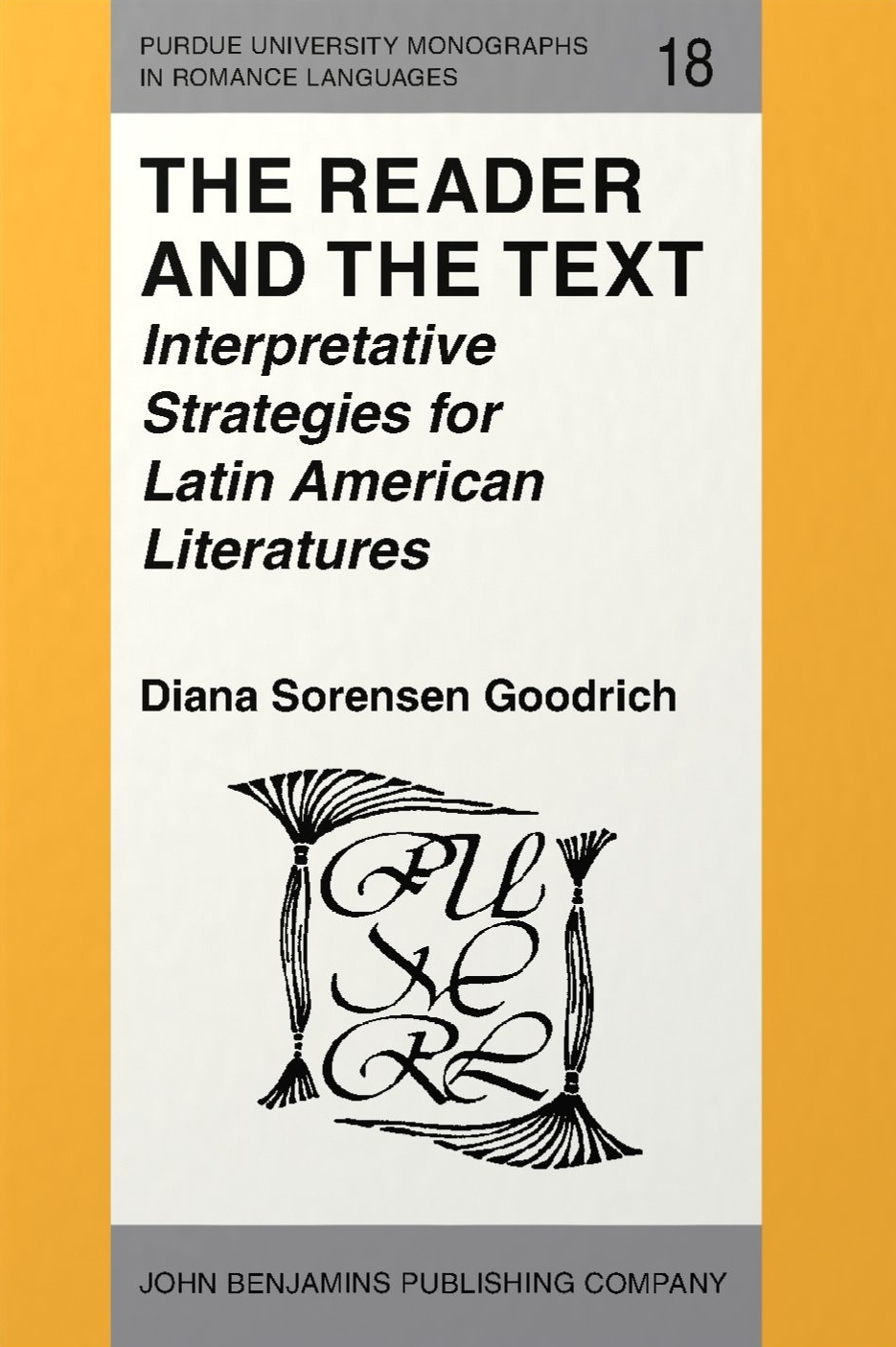讀者其實並不易為,費希 (S. Fish) 認為一個理想的讀者應是「(1) 一個對構成那篇作品的語言運用自如的說話者;(2) 一個完全掌握了『一個成熟的聽者竭力想理解的語文知識』的人;(3) 一個具備文學能力的人」,換言之,「他具有足夠的閱讀經驗,以至於把文學話語的各種特性全部內在化了。」
王忠勇:《本世紀西方文論述評》書影
文/陳炳良
最後一層是文類或文本互涉。當讀者明了作品主題之後,便可和同一類的作品互相印証,互相發揮。這也可說是進入了主題學或比較文學的範圍了。
〈月夜〉第四句的「蟲聲」出自《詩經.雞鳴》的「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它說明了女方盼望枕邊人早日回歸。「新透綠窗紗」的「新」是女方驚覺孤單的訊號。同時,蟲聲擾人,難以入夢,回應了第一、二句。夜深不寐,加上第三、四句對性與愛的暗示,使人想起〈關雎〉「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這兩句詩。「蟲聲」句又令我們想到六朝〈讀曲歌〉的「春風不知著,好來動羅裙。」蟲聲春風都挑起詩中女子的情慾。正所謂「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啊!(李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亦出自同一機杼。此外,綠窗是閨房的借代。李白的「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烏夜啼〉〕,溫庭筠的「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菩薩蠻〉〕,韋莊的「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菩薩蠻〉〕和「夜夜綠窗風雨,斷腸君信否」〔〈應天長〉〕可以作為佐証)。
以上五層,由淺入深。先從文字入手,如果基礎打得不好,文字的敏感度便低,對文本的意義便難於掌握。有些人極力排斥形式主義方法,就是因為不明白「輿薪有所不顧,而秋毫有所必爭,誠貴乎其專也」的說法。 [34] 跟著便是識力。所謂識力,它包括學識和智慧。朱熹說:
今人所以事事做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個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作不好底,不好底將作好底,這個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 [35] (〈答鞏仲至〉)
文中的「明」指知識,「識」指睿智。只有前者,欠缺後者,便如元湯垕《畫論》所說:
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紀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不過為聽聲隨彩,終不精鑒也。 [36]
章學識亦認為「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 [37] (〈與汪龍莊書〉)
現在嘗試以戴叔倫〈蘇溪亭〉為例,分析一下。
蘇溪亭上草漫漫,
誰倚東風十二欄。
燕子不歸春事晚,
一汀煙雨杏花寒。
層次一:七言絕句,正格。是一首描寫暮春景致的詩。
層次二:「倚欄」有盼望之意。如柳永的「想佳人、妝樓顒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欄干處,正恁凝眸。」(〈八聲甘州〉)
層次三:第二句「誰倚東風十二欄」是「修辭問題」(rhetorical question),「誰」實在是個浮動能指 (floating signifier)。作者這樣做,就強調了客觀性。它是一種「轉移中心」(decentering) 的手法,把感情非個人化。這合乎艾略特 (T. S. Eliot) 所說:「詩不是情感的放縱,而是情感的迴避。」 [38]
杏花因擬人化 (personification) 而能感到寒冷。但這寒冷實在指整首詩的氣氛。亦是詩中的「誰」所投射的。
層次四:本詩的主題也是閨怨。分離-盼望-孤單,可說是閨怨詩的三元素。
層次五:「草」象徵離別。原典出自淮南小山〈招隱士〉的「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第三句的意思是「如果對方還不回來,我快要人老珠黃了。」它和謝朓的「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王孫遊〉)比較,就更為含蓄,亦後出轉精的緣故。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 Logic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上面已說過,讀者自動憑其識力,提出疑問,使文本字面所未能指出的含義呈現出來,這是英加登所謂「具體化」(concretization)。 [39] 伊瑟爾進一步認為文本留有空白(blank),讓讀者憑其聯想力去填補。為了要吸引讀者,作者在文本中留有些缺口,叫它做「呼喚的結構」(structure of appeal)。 [40] 所以,「空白」不僅不是文學文本的缺點,而恰恰是它的特點與優點。其實,這是閱讀過程的一般現象-這現象包括期望-挫折-調整-期望……。朱立元說:「在閱讀中,這種舊視界常被文學文本打破──即『否定』,這時會產生一種思想上的『空白』,需要通過進一步閱讀獲得一個新視點,改變舊有的視界,來征服這個『空白』。」 [41] 堯斯把「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 稱為「期望視界」(horizon of expectation)。 [42] 當讀者的期望遇到挫折時,他會提出疑問。憑著他的識力,加上文本的幫助,他擴闊和提升自己的視界,結果達至了讀者視界和作品提供的視界的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 [43] 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五說:
學成於眾,新故相資而新其故;思得於永,微顯相次而顯察於微。 [44]
馬其昶在《古文辭類纂標注序》也說:
若夫古人之精神意趣,寓於文字中者,固未可猝遇,讀之久而吾之心與古人之心冥契焉,則往往有神解獨到,非世所云云也。 [45]
他們的意見也和「視界融合」說法,彼此一致。
舒非〈窗外紅花〉也是個好例子。 [46] 作者用平淡手法描述一個從大陸來港的女主角接到同學的電話,勾起了以前對他暗戀的情懷和前次之會面的回憶。這些回憶雖然未必美好或甜蜜,但卻並不苦澀。所以讀者會期望她再去赴約。可是,情節忽然來個逆轉,她決定不赴約。她的舊友只得很無奈地說:「好吧,不再打攪你了。」這個結局令人意外。作者對女主角的決定並沒有任何解釋,這就是「呼喚的結構」。目的在使讀者提供自己的意見。一般讀者會覺得女主角性情古怪,行為乖僻。但一些了解傳統婚姻道德的讀者,就知道她所以爽約是因為不想瓜田李下,儘管丈夫對她的暗戀甚至約晤的事,一無所知,她還是刻意地避嫌。這使人想起張籍的〈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
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
繫在紅羅襦。
……
知君用心如日月,
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
恨不相逢未嫁時。
舒非提出了一個道德問題,迫使讀者去思考。同時,這也不單涉及道德問題,還和作品的藝術成就牽上關係。這可說是一種「韻外之致」。
由此,我們可以見到在〈窗外紅花〉的閱讀過程中,讀者的期望視界和作者/作品所提供的視界就融合起來。從閱讀層次而言,是由第五層次的文本互涉來幫助了解它的主題──傳統已婚婦女的道德的問題。而第五和第四個層次的互動關係亦同時顯現出來。
關於文本互涉在閱讀中所起的作用,顧德麗 (Diana Sorensen Goodrich) 曾加以討論。她認為:從經驗上說,文本互涉是讀者能力的作用之一;但從理論而言,它包括認取和記取讀者心中的文學百科的前文本 (pre-text),其後,前文本和文本間產生了意義的擴散。作為文本互涉的作用者 (intertextual operator),它可能是明顯的,也可能是隱晦的。這是說,它可能被認出是指向一源頭的信號,或許它是「秘響旁通」,或是披上偽裝。而對它加以披露是讀者能力強有力的表現。總言之,文本互涉不是用作後設文本 (metatextual) 的評論,而是提供一個基本結構來說明所要討論的文本只是它的一個主題變奏。 [47]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for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s”
戴叔倫「燕子不歸春事晚」中的「不歸」就暗指(「秘響旁通」)謝朓的「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這說明戴詩的基本結構是閨怨。〈節婦吟〉是偽裝的「文本互涉作用者」,使讀者了解〈窗外紅花〉的道德意義。這說明了文本意義的互相擴散。因而使讀者能創出文本意義來。
綜括來說,閱讀文學作品時,雖然「各以其情自得」(上引王夫之語),但實在不至於泛濫無歸。為甚麼?因為讀者要憑知識和睿智(識力)去闡釋文本;有了知識的限制,讀者便不能信口雌黃了。葉燮說:
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為濟,苟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無識而有膽,則為妄,為鹵莽,為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無識而有才,雖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顛倒,才反為累也。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誤人而惑世,為害甚烈。若在騷壇,均為風雅之罪人。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為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為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寧獨在詩文一道已也? [48]
他說的雖以作者為對象,但我們何嘗不可把讀者也包括在內?
至於「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的原因是作者寫作之時,因種種關係,寫成的作品和原意可能有了距離。清張庚《浦山論畫》說:
氣韻有發於……意者,有發於無意者。發於無意者為上,發於意者次之。……何謂發於意者?走筆運墨,我欲如是而得知是,若疏密多寡,濃淡乾潤,各得其當是也。何謂發於無意者?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謂之為足,則實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蓋天機之勃露也。然惟靜者能先知之,稍遲未有不汨於意而沒於筆墨者。 [49]
「謂之為足」至「天機勃露」幾句,亦可借以描述上面討論過的〈窗外紅花〉中結尾的「呼喚的結構」。
此外,鄭燮也反對我們對「胸有成竹」的一般看法。他說:「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其實胸中之竹,並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50] (這和伊澤爾所說,當我們引發回憶,回憶和原初印象並不相同的說,大體相似。 [51] )
既然作者也在有意無意間完成他的作品,讀者當可不必去探索他的原意了。
總的來說,讀者其實並不易為,費希 (S. Fish) 認為一個理想的讀者應是「(1) 一個對構成那篇作品的語言運用自如的說話者;(2) 一個完全掌握了『一個成熟的聽者竭力想理解的語文知識』的人;(3) 一個具備文學能力的人」,換言之,「他具有足夠的閱讀經驗,以至於把文學話語的各種特性全部內在化了。」 [52]
當然,費希的要求或許是陳義過高,但我們不妨把它作為我們向前努力的指標。
[本文原刊於《文學論衡》第20期2012年2月。]
[34]〈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章氏遺書》卷二十二,頁221。
[35]轉引自張思齊:《中國接受美學導論》(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頁121。
[36]見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神州國光社,1947年本) 三集第七輯。
[37]《文史通義》,外篇三,〈與汪龍莊書〉,頁82。
[38]參王忠勇:《本世紀西方文論述評》(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204。原文見 T.S. Eliot,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2),p.21.
[39]參《接受美學》,頁372-379。英加登亦提及「不定點」(places of indeterminacy), 見 op. cit., p.13; 中譯本,頁14。又參考 Roman Ingarden,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 Logic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tr. George G. Grabouicz) (Evanston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pp. 246-254.
[40]同上書,頁22-23。
[41]同上書,頁24。
[42]同上書,頁13-15,133-134。參《批評的循環》,頁88。
[43]詳參《批評的循環》,頁120-126。朱立元說,「從發展角度看,文學接受就是個人或群體置於傳統之內,讓過去舊有的視界與現在的新視界不斷碰撞交融,從而達到新傳統的形式或舊傳統的更新發展。」《接受美學》,頁174。
[44]見《船山遺書》(華文書局影印本),卷五,第五章,頁14b。
[45]﹝清﹞馬其昶:《抱潤軒文集》,光緒刊本,卷四,頁 12a -b。
[46]刊於《星期天周刊》26期, 1994年6月5日 。
[47]Diana Sorensen Goodrich,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for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86), pp.57-73.
[48]﹝清﹞葉燮:《原詩》(《清詩話》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內篇下,頁584。
[49]見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北京: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7年),上冊,頁225。
[50]﹝清﹞鄭燮:《鄭板橋集》(香港:中華書局,1962年),頁161。
[51]Iser, op.cit., p.278.
[52]《讀者反應批評》,頁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