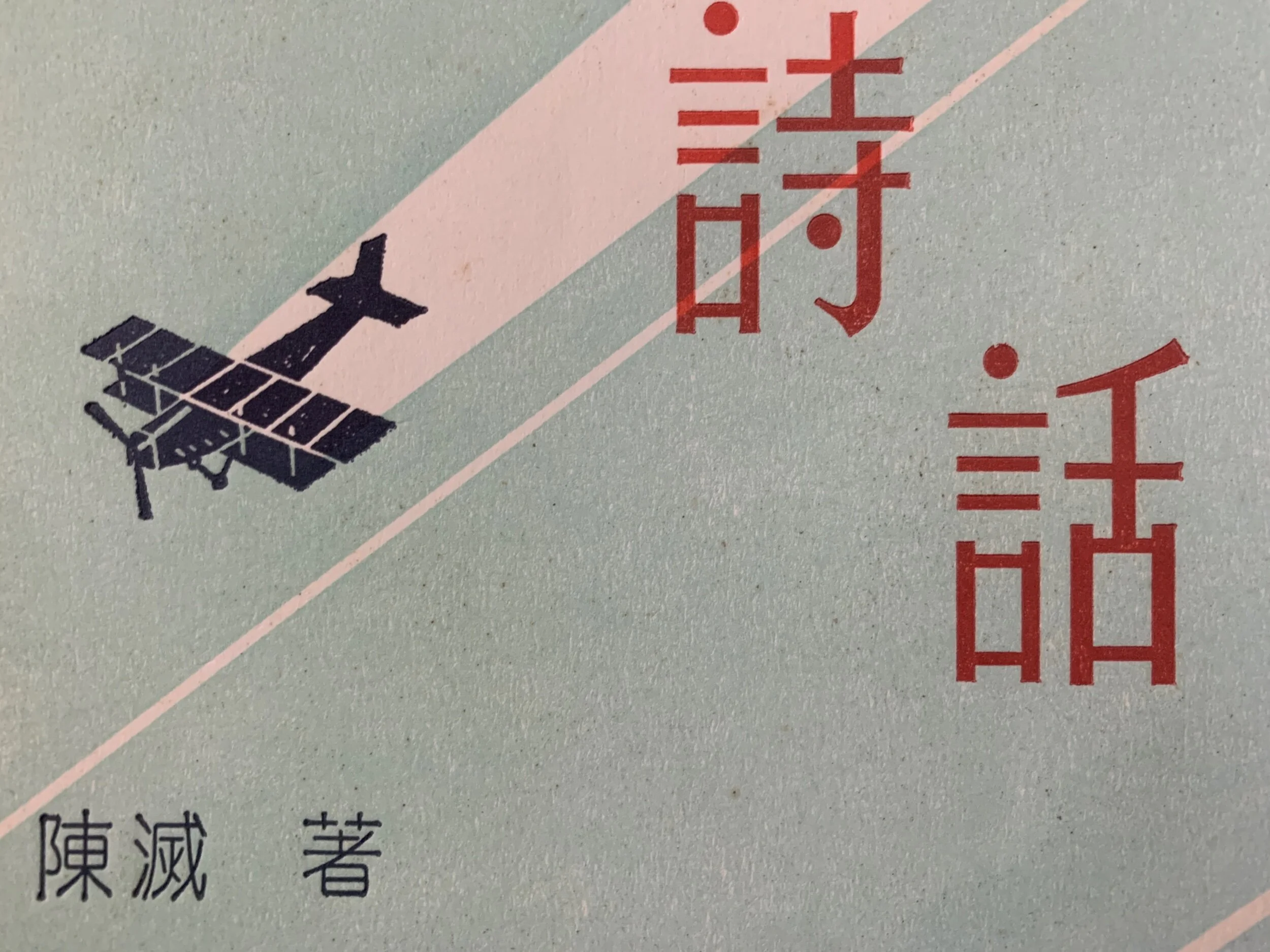「雖然我不知道在哪裡停留,但我相信希望永遠在前頭。」為甚麼明歌選擇了戲劇這種形式?戲劇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基於現實,超於現實,在重複中尋找差異,在間隙中察視希望所在。
曾雪儀作品《漂流到北京》
文/賴勇衡
一次離地閱讀之得著
為甚麼這時要讀一本以2008北京奧運前夕為背景,以外省民工子女為主角的小說?
香港人自己的問題已經夠煩了,每年都感到是危急存亡之秋。那麼十一年前一個發生在北京的故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京奧彷彿已是遙遠的過去;當年耗費甚鉅的體育場館已成廢墟[1],而無數參與建設的工人被視為「低端人口」[2],同樣用完即棄,就如《中英聯合聲明》,只是「一份歷史文件」。
2008年,對一些人來說是盛世之端,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衰落之始。北京奧運,萬國來朝之象,預示著「一帶一路」天朝擴張的野心。這是兆始之年。那一年,因為四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香港人對中國的身份認同感到達頂峰,之後每況越下;今天很多香港人感到最焦慮的事,就是「北京」成為此時此地。
《漂流到北京》是歷史的切片,就在個人/時代之間,亦在我們/他們之間,「若即若離」是它的關鍵詞,直指人的存在狀態:既不及時(timely),也不過時,亦唔知等到幾時。故事有關一個廿多歲的香港女子在北京一家農民工子弟學校當義工,負責戲劇興趣小組,以散點透視的方式牽引出不同民工子弟的故事。他們在盛世食物鏈的下游,當中有的人間蒸發、有的更上層樓。故事由作者曾雪儀的親身經歷及見聞所改編,而現實比小說更曲折:小說其中一位主角,天資聰穎的少女丁鈴最後獲資助入讀藝術學院,其原型本尊卻於數年前突然病逝。這件事令人想起丁鈴惦記著的一個故事,更是唏噓:
「老師說,當人們看到發光的星星時,其中有些可能已經死去,因為消亡的光輝歷經多年才來到地球,就像一個人死前寄出一封信,許多年後才送到收信者手中,那時候寄信的人已不在了。」
寄信的人已不在了。她已經成了一個胡琴星座。死去的人永不怕過時。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不合時宜的閱讀
羅蘭巴特說:「當代者不合時宜。」阿甘本在 〈甚麼是當代〉[3] 一文中寫到,當代性就是一個人與其時代的獨特關係,既依附之,又抽離之,驀然回首,才能凝視自身的時代。《漂流到北京》的主要角色,不論是來自香港的明歌,還是來自中國各省的民工子弟,與北京都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民工在家鄉大多失去農地,只能在大城市謀求發展,卻在自己的國家永遠當個異鄉人,為其光輝貢獻了血汗,卻被視為異類。其中沈氏一家,父親本來是建築工人,因意外成為殘障,只能轉行撿破爛,一家住在廢品場。「廢品」既可回收再造,就不算廢物;所以沈爸爸成為了所有農民工的象徵:明明有價值,卻又被貶斥——這不是隱喻,而是真實。
農民工子弟要不在農村留守,就是跟父母在大城市中求存,但北京的公立教育並不歡迎他們。有些私立的農民工子弟學校由有心人所創辦,讓他們接受教育機會,但不一定合乎當地法例。即使有些民工學校按政府要求註冊,仍會隨時被逼遷封校,苦無路訴。失學的民工學生唯有回鄉,或出來工作——直至再被逼遷。《漂流到北京》的背景是08年,但上述的壓迫到今天仍未休止[4]。流離 (precarious)成了一種恆常的狀態,而這狀態並不只是北京農民工才須面對,而是全世界中下層共同面對的處境。
Photo by Steve Long on Unsplash
《漂流到北京》本來定位是青少年小說,當中的人物,不論是來自香港的明歌還是其他民工子弟都在一種前路不明的處境裡,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尚在轉化之中、晦暗不明的閾限狀態。明歌帶領的戲劇小組最後演出以這句台詞結束:「雖然我不知道在哪裡停留,但我相信希望永遠在前頭。」為甚麼明歌選擇了戲劇這種形式?戲劇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基於現實,超於現實,在重複中尋找差異,在間隙中察視希望所在。可惜小說中對戲劇小組的描寫著力不深,縱使在故事中提及二胡演奏和豫劇等表演藝術,卻未探討演藝與人生和現實的關係。
明歌這角色的身份來歷亦是點到即止。她為何要到北京當義工,並以農民工為服務對象?作者並未詳細解釋,這方面的省略卻突出了明歌這個香港人和那些外省學生的共通點:他們都在晦惑之海漂流。作為比較年長、學識和閱歷稍稍佔優的青年,她是個覓路人,也是個提燈者,與民工子弟們同路摸索。然而他們不知道,晦暗不明的階段還會持續多久,沒有人能保證那不是永遠。
在故事裡農民工父母的經歷中可見,原來不穩定、不清晰的生存境況並非青少年獨有。他們離開家鄉,不一定在工廠有穩定收入,而是從事家庭手工業、小食攤販、廢品回收等「做得一日得一日」的工作。對今天的香港人來說,無論北上發展事業、移民外地逃避即將踏下來的鐡靴,還是被融入大灣區中,都和農民工一樣,總在流離,無法生根。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趨勢下,勞動者生活無保障,中產擔心下流,望子成龍的欲望又抵不過「成功需父幹」的鐵律;依靠公共福利的人,又因節約措施(austerity)或私營化的謀利思維而被進一步排斥。越來越多人成為立在浮沙之上的漂流者。《漂流到北京》角色眾多,一個個出場,如《清明上河圖》的散點透視。然而小說描繪的是一條流沙河的下游,人們掙扎著、憂慮著福禍難料之未來:沈夢洋跟隨叔父介紹的女子往河北工廠打工,從此失蹤;因為她是沒有登記的「黑戶」,政府也愛莫能助,肝腸寸斷的母親或許只能在夢中與她再見。孤兒菊婷獲善心人「黃叔叔」資助入讀職訓高校,後來他卻露出齷齪之相,菊婷憤而與他決裂。當然還有那在小說世界以外玉蕭聲斷的「丁鈴」。或許希望一直只能是希望 — — 直至絕望。
Photo by Yingchih Hao on Unsplash
若絕望就是純粹的、永恆的黑暗,我們便會被阿甘本所提醒:雖然不合時宜的「當代者」凝視著時代的晦暗而非光明,但當代性仍讓我們從晦暗中辨認出一種永遠看不見、卻總是在趨近的光芒,就像在不斷膨漲的宇宙中射向我們的星光。先知,是說出了這束光之臨近時仍未看見光的人。「當代」的文藝作品都應有這種先見之明,但凝視晦暗的不只是作者,也是讀者。當讀者翻開書頁,不合時宜的閱讀讓過去與將來都在當下敞開。
今日我在倫敦重讀十年前在香港出版的《漂流到北京》時,也在網上看到重新走上街頭的香港人,從鳥瞰角度看到像螞蟻般小,不禁想起2003年那個令人腳痛的夏天。這本書沒有過時,即使2008年不斷遠去,像因宇宙膨漲脹而高速離開我們的星體,當中銘刻了那一年如何揭開一個只屬於一小撮人的盛世;即使奧運場館已荒廢,同樣的剝削邏輯卻往西方一路複製。但有人仍在紀念那些螞蟻。小說第一章,丁鈴的床頭有一列螞蟻鍥而不捨地行進;螞蟻走到結尾,走進了她的夢中,卻只剩下一隻在泥上打轉。牠們早已四散,在尋找自己(可進入)的夢。我也想到倫敦街頭那些無家可歸的人,當中仍有人發著舞台演員及電影導演的夢[5]。這本書提醒我們都是在巨輪之下流離的螞蟻,穿越夢與現實之間——但願不要走進噩夢之中。若然被輾碎,仍未毁滅,而是成為星叢之一,在晦暗的宇宙中發出永遠在旅行的光。
作者簡介:賴勇衡,香港基督徒,倫敦大學國王學院電影研究系博士生,戲劇、電影評論人,網誌「我不是貓」。
[1] Beijing’s eerie abandoned Olympic venues
[3] Agamben, Giorgio. "What is the Contemporary?” In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p.39–54.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5] 賴勇衡:〈不做鹹魚: 睡在街頭的導演和演員〉。刊於《am730》2018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