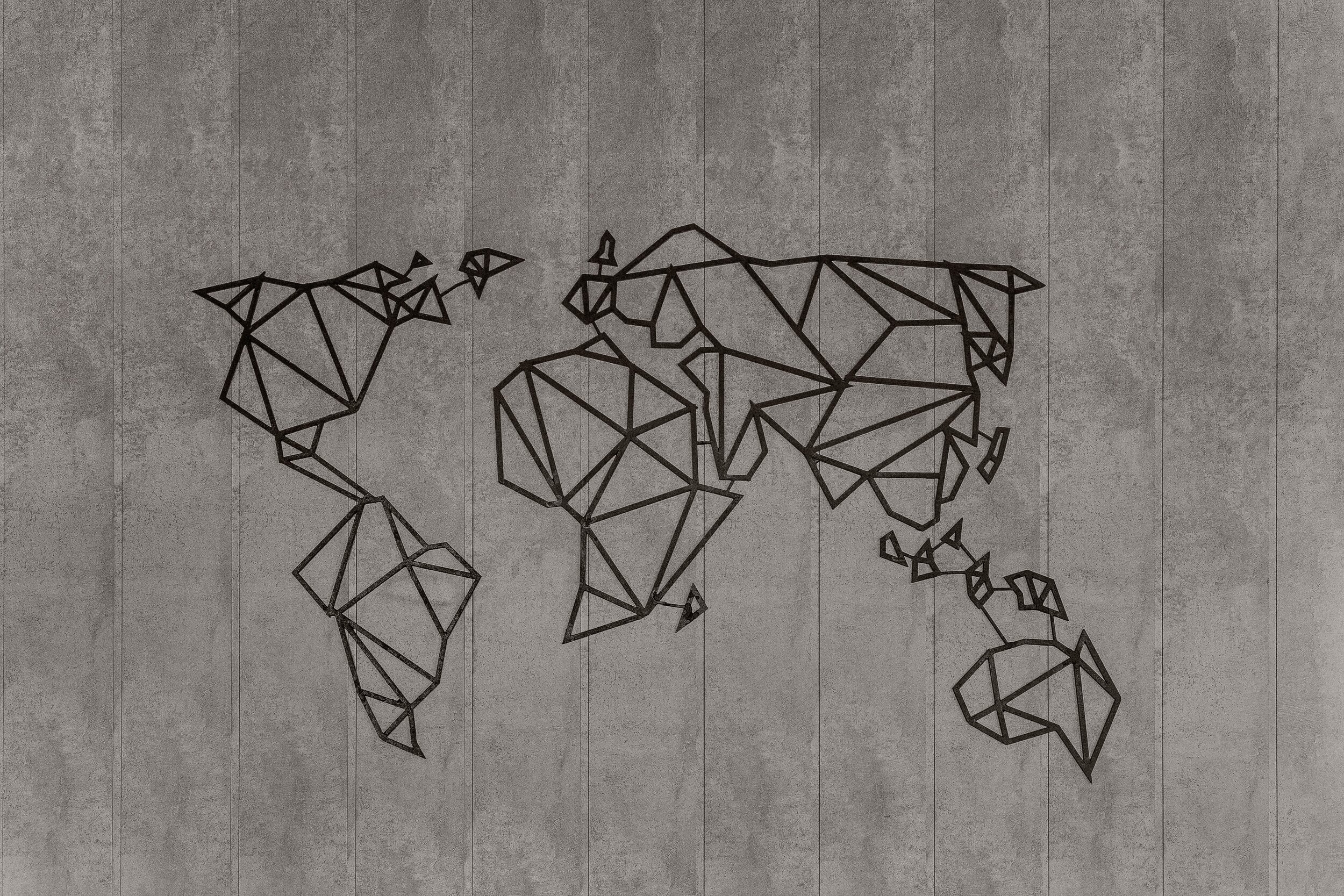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Photo by Ben Sweet on Unsplash
受訪者:蔡元豐 教授
訪問者:吳廣泰先生
筆錄及整理:徐竟勛先生
訪問日期:2020年11月26日 下午4時(以ZOOM進行視像訪問)
病是生命的故事
吳:那麼,如果疾病回到自然本身,會不會喪失了它本身的文化意涵?文化背後的東西會不會就此消失?
蔡:這個問題的關鍵詞是「自然」和「文化」,譯成英文就是nature與culture。我們習慣將這兩個概念二元對立,認為「自然」就不是人為的,而「文化」是人為的,不自然的。我跟文學院的同事剛剛辦了個人類世(Anthropocene)國際研討會。「人類世」是地質學名詞,關乎人類如何影響地質。在香港移山填海,要勘探地質,過去發現的花崗岩未來在將軍澳堆填區將會是垃圾,人類留下的各種廢料已經成為地殼最表面的一層。人類世學者大多注意氣候變化,溫室效益與工業文明息息相關,人類「文化」其實已經影響了「自然」,人與自然密不可分,「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故此,當疾病回到「自然」本身,並不會喪失其「文化」意涵,反而更能看清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正如疫情,不單止回應自然,也回應了文化與制度。疾病當然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如何反應、處理,都會影響疾病的自然狀態。禁止散播「謠言」,反讓病毒流傳。
吳:所以人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蔡:對,這個概念類似道家哲學的自然觀,二而一,一而二。
Photo by Марьян Блан | @marjanblan on Unsplash
吳:文學往往將疾病視為隱喻,此外尚有其他可能嗎?
蔡:從修辭學和語言學來說,提到隱喻,便會想到換喻。隱喻把兩種不相干的東西放在一起,而換喻則是部分與全體的關係,如用「寶劍」換喻「武士」,用「機翼」換喻「飛機」。防疫與「戰爭」是隱喻的關係。就換喻而言,魯迅本來學醫,同時他本人百病纏身,身為病人,除了用疾病隱喻文化,晚年論戰時雜文中罵人的脾氣也許受到肺病影響。另一例是史鐵生,由〈我與地壇〉到《病隙碎筆》,作品中那些對於人生無常的感悟,其實與他的癱瘓和腎病直接關連。再舉外國文學為例,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啟迪》(Illuminations)中分析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認為普魯斯特的句式及節奏其實是出於他對哮喘病窒息的恐懼,哮喘的節奏感成就了普魯斯特的節奏感,疾病與藝術相輔相成,發生共生關係(symbiosis)。[1]
二零一六年,香港的傑出表演藝術家陳麗珠搬演了英國劇作家莎拉‧肯恩(Sarah Kane,1971-99)的遺作《莎拉‧肯恩在4.48上書寫》(4.48 Psychosis)。據統計,凌晨四點四十八分是自殺率最高的一刻。原著描述人的失眠狀態,由抑鬱到瘋癲,間雜多段緊張的醫患對白。陳麗珠當時以獨舞形式表演了這齣疾病誌。肯恩說:「沒有一種藥,可以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佛家曰「生老病死」,疾病其實就是生命的換喻。接受換喻,就是視疾病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來,〈狂人日記〉中狂人的焦慮其實也代表了魯迅一生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