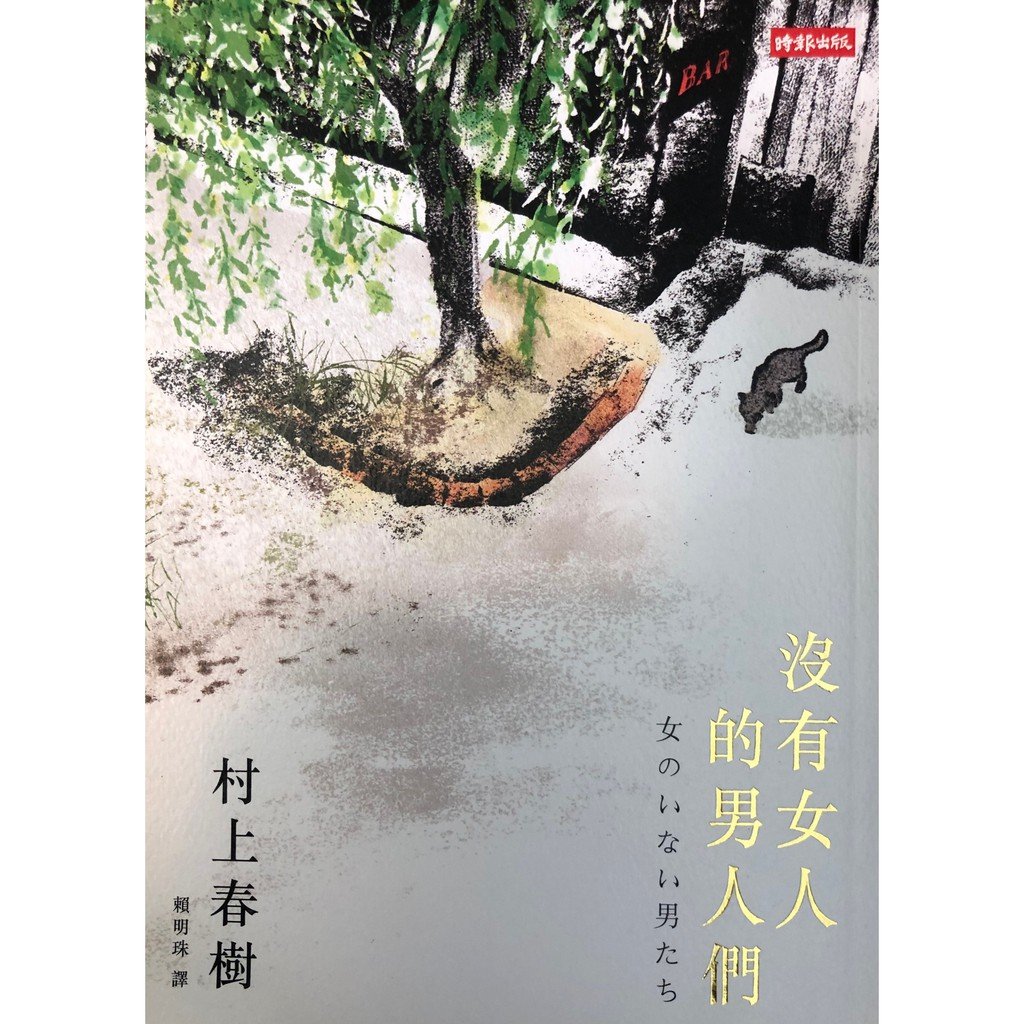電影刻意在末段將《Drive》《凡》的人物關係並置,安排美紗紀與家福在雪地的對話,與家福以舅舅角色感受著桑尼亞 (允兒) 的台詞,以兩組鏡頭順序排列,彷彿《凡》那盼望永生的信仰,就是《Drive》面對過去苦難的答案。
文/查柏朗
在路上,不歇息,前面等待著的是無盡的孤獨,但也會是自由的可能。”Drive My Car”本只是性邀約的暗示 (Beatles流行曲),或延伸為男人對女人的不解 (村上春樹的短篇),在濱口龍介的改編下,終於借助其影像形式,呈現這行動的意義。駕駛著車,重點是行駛向前,不是停步或倒退的狀態 (不停在目前、不回望過去),正是對待生命的態度; 這又巧妙地呼應著契訶夫《凡尼亞舅舅》的最後,桑尼亞跟舅舅說,到死後就/才可得著安息。
《Drive My Car》改編自村上春樹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同名篇章。
村上《Drive My Car》筆下的美紗紀曾指自己「不太美,就像桑尼亞」,濱口版本則不止於這外表的聯繫,還添補了她駕車不睡的設定,擴充了其家庭背景的悲劇,讓其更貼近於桑尼亞的辛苦勞動、離不開莊園的困境。基於這前提,美紗紀逐步打開心扉的過程,漸漸與原著小說講述男主角家福的故事並行成雙主軸。
跟濱口前作《睡著吻別醒來抱擁》女主角唐田英里佳的演出要求一樣,美紗紀的原設就是欠缺表情,既是司機平穩的專業展示,亦是蓋掩真性情的面具,同時與片中其他演員角色的豐富表演作對照。《Drive》最能以影像去表現文字描述美紗紀的駕駛技藝的一場戲,是情夫高槻車內跟家福剖白,全程只是對剪著兩男的對答,觀眾及主角全情專注於高槻所說,鏡頭沒有掃過美紗紀,亦沒有大幅度的移動,直是「忘了身在車上、忘了司機在場」感受最精準的傳譯。
《Drive My Car》改編自村上春樹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同名篇章,導演濱口龍介憑此勇奪第74屆康城影展最佳劇本獎。
美紗紀與家福的微妙變化亦因而轉以行為的調整來呈現。像等待家福時,堅持不上其車,到後來與他約定,有需要時就進車內; 家福由開首總是坐後座,到與高槻車內坦然道別後,走上副駕駛位置,拉近與美紗紀的距離; 吸煙的限制慢慢放寬,由無煙環境,到開車窗,然後是開篷的兩煙向天。影像上穿過重重隧道,直到聲音上抵達「什麼都沒有的地方」之寂靜,就是兩者心靈最貼近的瞬間。
電影刻意在末段將《Drive》《凡》的人物關係並置,安排美紗紀與家福在雪地的對話,與家福以舅舅角色感受著桑尼亞 (允兒) 的台詞,以兩組鏡頭順序排列,彷彿《凡》那盼望永生的信仰,就是《Drive》面對過去苦難的答案。然而一如家福所言,契訶夫的劇本,取決於演繹者本身 (以允兒與Janis的排演,將原來女兒與後母關係轉化為情慾流動),舞台上的家福 (西島秀俊的演出) 面對著允兒肯定的手勢,反應並非相信,而是臉上滿佈疑惑,允兒與家福兩者不調和的表演,連繫全片反復強調跨越言語限制的肢體力量 (多國語言及手語交流),就見濱口怎樣以演員的身體,去表現《凡》文本不同閱讀方向的反差,那『「就」與「才」可安息』的一線之差。
出走南韓的結局進一步確立其曖昧。從表層看,美紗紀離開了日本,似是拋下過去重新開始,載著似乎是家福送給她的車 (同時意味著家福放下妻子),但家福不再在場,同樣表示她已遠離一段曾讓她卸下心防的關係。關鍵是她帶著同行的狗,全片有狗現身的段落,都是她逃避真情流露而遁去逗弄小狗的離場方式。第一次是與家福首趟同檯吃晚飯,在此之前她在電影幾乎沒有特寫,或置身黑暗燈光背景,看不清容貌,是次跟家福並排而坐,還得到其正面認同,鏡頭首次停留其臉上的光,她卻不知怎作回應,於是離開鏡頭視線,稍後攝影機再次移向她,就發現她與狗在玩耍; 第二次她與家福在海邊聊天,同樣是狗令她分心,沒再將話說下去。於是向前走、不休息的狀態,是否仍是她帶著心結的封閉自我?
但這不該被視為純粹的絕望,也絕非積極向上的光明,或許是兩者之間游走的不確定,或許是木野所說的二義性 (《木野》也是濱口是次改編村上作品之一),或許就視乎代入文本的人怎樣想,怎樣去延續這演繹。
作者簡介:查柏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及「香港樂評選」成員,社交媒體專頁「查柏朗的名單」版主,主力影像及音樂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