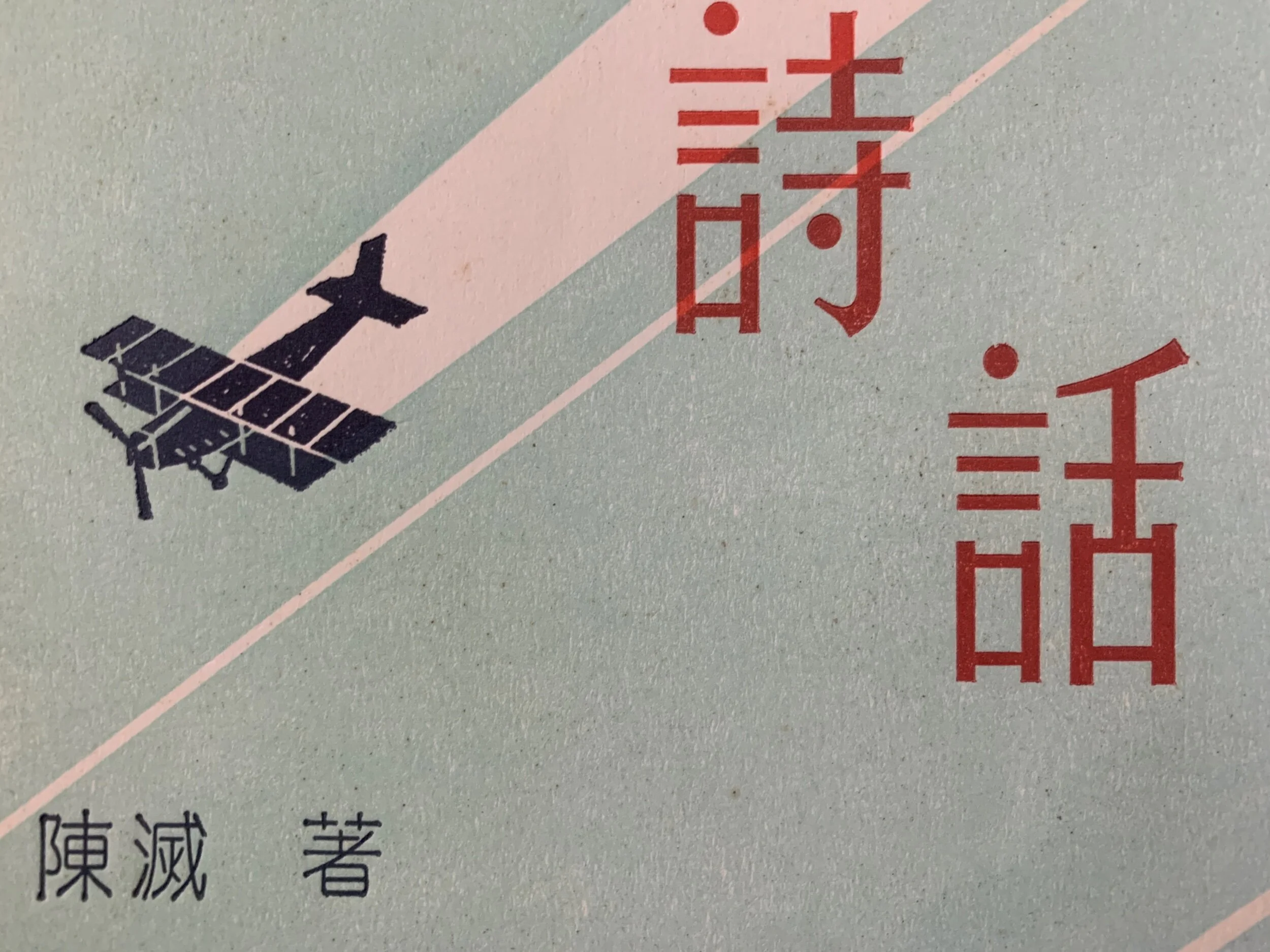文/葉輝
話說四卷本的《熊秉明文集》借出經年,竟有借有還,信是稀有書緣,與熊秉明三十多年前有一面之緣,他客居中大宿舍,暢談春日的「是」,夏日的「有」,談一個下午,意猶未盡;忘了問他:在西南聯大唸哲學系時認不認識鄭敏?外文系的穆旦?盧飛白(李經)?生於1922年的熊秉明比鄭敏、盧飛白年輕兩歲,比穆旦年輕四歲;另一西南聯大詩人艾山(林蒲)比他年長九歲,1938年已畢業,兩人合該沒見過面。
那一次跟熊秉明見面,朋友帶其著作讓他簽名,我喜歡他的《關於羅丹--日記擇抄》,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有此說法:「羅丹是一切--」熊秉明認為:「羅丹用那麼多千變萬化的雕像,給讀者看可悲可喜可歌可泣可愛可怖的種種相」;讀過里爾克《羅丹論》(Rodin;Auguste),熊秉明《關於羅丹--日記擇抄》以及《看蒙娜麗莎看》,讀得極有興趣,讀出許多關於觀看的學問。
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他說中國人對雕塑和人體都很陌生,對我來說倒切中要害--他的「觀看之道」可用「我在其側,我在其中」以概括,僅在其側不夠,不在其中則無從入乎內而出乎外了,大抵亦為約翰伯格(John Berger)看畫方法;他在《中國書法理論體系》說得好,「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從抽象思維回歸到形象世界的第一境的可以說是書法。書法的素材是文字,亦為抽象思維運用符號」,其賈此為三位一體--哲學,詩境,書法。
熊秉明一生只寫三篇詩論,《論一首朦朧詩——顧城〈遠和近〉》也許對朦朧詩還沒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但那一篇文章卻能從一首詩談到存在主義的精神,從而闡發層層推展的思維組織,與他論余光中《蓮的聯想》的「三聯句」、林亨泰的《風景(其二)》一樣,論得透剔通達,處處閃爍語言藝術的真知灼見,三論的洞見乃一脈相承的澄明與圓融。並非由於他比別的論者聰明,只是由於他對所討論的作品下過工夫,讀得比別人更仔細更深入,似有所悟,從雕塑到詩,從哲學到書法,許是類觸旁通、出入於形象與抽象,當中涉及宗白華的《美學散步》。
西南聯大很了不起,孕養很多詩人,熊秉明詩名不大,詩倒也寫得很有味道,比如這一首《黑板.粉筆.中國人》:「我的頭髮一天一天/從黑板的顏色/變成粉筆的顏色/而且像粉筆一樣漸漸/短了 斷了/短成可笑的模樣/請你告訴我我究竟一天一天更像中國人呢/一天一天更不像中國人呢/這是黑板/這是粉筆/我是中國人」,簡約的比喻,深刻的人生寫照,與《珍珠》對讀,兩詩恍若相互的變奏:「我每天說中國話/每天說:/這是黑板/那是窗戶/這是書/如果舌頭是唱片/大概螺紋早已磨平了/如果這幾句話是幾粒小沙/大概已經滾成珍珠了」。
詩與畫如鏡子
在宗白華《美學散步》有《詩(文學)和畫的分界》一文,詩與畫有如鏡子,王昌齡《初日》詩云:「初日淨金閨,先照床前暖;斜光入羅幕,稍稍親絲管;雲髮不能梳,楊花更吹滿」詩中境界很像一幅近代印象派大師的畫,畫裡現出晨光射入的香閨,日光在此畫為活躍的主角,從窗門跳進來,跑到閨女的床前,散發一股溫暖,穿進羅帳,輕撫榻上的樂器——閨女所吹弄的琴瑟簫笙——枕上如雲的美髮散開,楊花隨著晨風春日偷進閨房,躲上枕邊的美髮;此詩並無直接描繪少女(雲髮兩字僅為暗示),一切的美是歸於看不見的少女。
王昌齡此詩讓讀者浮想連篇,甚或想起德國畫家門采爾(Adolph von Menzel)的油畫,畫上為燦爛晨光,從窗門撞進一間臥室,乳白的光輝浸漫在長垂的紗幕,落在地板,返入穿衣鏡,又從鏡中跳出來,撫摸椅背,感到晨風清涼,朝日溫煦,畫面看不見臥室的女主人,她或坐在屋角的床上。
Balcony Room Adolph von Menzel, 1847 畫中無人,右邊有一面鏡,反照室內動靜。
那畫面就像一首詩,當中包藏一些不為人知的往事;一如阿拉貢(Louis Aragon)的詩作《鏡子前的艾爾莎》(Elsa au miroir):
我們的悲劇正處在高潮時刻
漫長的一天裡 她坐在鏡前
梳理著她的金髮我彷彿看見
她堅忍的手平息著一場戰火
我們的悲劇正處在高潮時刻
漫長的一天裡她端坐在鏡前
梳理著她的金髮我或許會說
我們的悲劇正處在高潮時刻
她彈著豎琴對曲調不以為然
整整漫長的一天她坐在鏡前
梳理著她的金髮我或許會說
整整漫長的一天她坐在鏡前
她恣意地把自己的記憶熬煎
又燃起戰火中那無盡的花朵
而換個女子會說的她卻不說
她恣意地把自己的記憶熬煎
我們的悲劇正處在高潮時刻
世界猶如這面鏡子那樣醜惡
梳子分縷著閃閃發光的火焰
那火焰照亮了我記憶的深淵
…………
當中情景,就教人想起卞之琳詩《魚化石》(一條魚或一個女子說):「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我往往溶化於水的線條。你真像鏡子一樣的愛我呢。/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據《魚化石後記》解釋,第一行化用艾呂亞(Paul Eluard)的兩行句子:「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狀,/她有我的眸子的顏色。」並與司馬遷的「女爲悅己者容」的意思相通;第二行蘊含的情景,從盆水裡看雨花石,水紋溶溶,花紋溶溶,令人想起瓦雷里(Paul Valery)的《浴》;第三行「鏡子」的意象,與馬拉美(Stephane Mallarme)所言「你那面威尼斯鏡子」互相投射,馬拉美描述,「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圍著鍍過金的岸;裡頭映著什麼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個女人在這一片水裡洗過她美的罪孽了;也許我還可看見一個赤裸的幻象哩,如果多看一會兒。」最後魚化成石的時候,魚非原來的魚,石也非原來的石了。這也是「生生之謂易」。也是「葡萄蘋果死於果子,而活於酒。」詩人又問:「詩中的『你』就代表石嗎?就代表她的他嗎?似不僅如此。還有什麼呢?待我想想看,不想了。這樣也夠了。」
鏡子心理學:恐懼與鏡影焦慮
世界瀰漫恐懼感,世人毫無安全感,故此在心理上湧現大量匪夷所思的「恐懼症」(phobia);《生活》(Life)雜誌就舉列出三十四種相當罕見而怪異的恐懼症,包括「詩歌恐懼症」(metrophobia)、「鏡子恐懼症」(catoptrophobia)、「恐雲症」(nephophobia)、「恐雪症」(chionophobia)等等--從詩歌到鏡子,再到雲和雪,舉凡引起詩性想像的事物,都會令有些人心存恐懼。
為何對詩歌心存恐懼呢?那大概因為詩人都不喜歡直話直說,總挖空心思,將一句簡單的話,說得複雜,此所以西方和台灣的現代詩、內地朦朧詩都難免艱澀,甚或會教人望而生畏;當中原因眾多,有些也許為迴避政治審查,有些為突顯「觀看的距離」、「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等等語言效果,久而久之,詩就逐漸遠離群眾了。然而,詩一如音樂,一如鏡中影像,有時必須要跟現實保持距離--說到詩與恐懼,或可用波蘭詩人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的《我們的恐懼》為例:「我們的恐懼/並不套著一件夜晚的襯衫/不具有貓頭鷹的眼睛/不是去掀開一個棺材蓋子/或熄滅一支尚在燃燒的蠟燭」,「甚至不具有一張死者的面容」;那麼,詩或詩人何懼之有呢?
赫伯特此詩說:「我們的恐懼/是在口袋中發現的/寫在紙上的一句話/『提醒伏契克/德勞加街老地方有危險』」;詩中所說的伏契克(Julius Fucik,1903 -1943)乃捷克記者兼作家,被納粹判處死刑,他在獄中遺著《絞刑架下的報告》(Reportaje Al Pie De La Horca)寫道:「我們為歡樂而生,為歡樂而戰鬥,我們也為歡樂而死。因此,永遠不能讓悲哀同我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此所以赫伯特所言的恐懼,實為對強權控訴:「我們的恐懼/不擁有一張死者的面容/死者對我們溫柔的/我們把他們扛在肩上/裹在同一條毯子底下」;「合上他們的眼睛/擺正他們的嘴唇/挖一個乾燥的坑/把他們埋掉」;「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淺」--「恐懼」也者,原來就是對強權「無畏無懼」;至於「鏡子恐懼症」,說來與詩或藝術師承問題相涉,匈牙利精神分析學家費倫齊(Sandor Ferenczi)有此觀點:「鏡子恐懼症」與「注視恐懼症」(scopophobia)有所關聯,兩者俱源於「自我意識」的恐懼,亦即對「自我影像」的逃避--此說該從何說起?那就要從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說起,此位心理分析大師對費倫齊來說,真是亦師亦友,但費倫齊的學說其後徹底遠離佛洛依德,當中何嘗沒有「鏡子恐懼症」或「注視恐懼症」成份?大概就是一種「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面對前行者的影響,猶如面對鏡子反照的重像,「鏡中人」既心存恐懼(或焦慮)又為之心神嚮往。
Nude in front of a Mirror 1897 土魯斯-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
Girl Before A Mirror 畢卡索(Pablo Picasso) 1932
Woman Before A Mirror卡塔拉(Luis Alvarez Catala) 1878
Before The Mirror 羅傑斯·尼爾森(Raymond Perry Rodgers Neilson) 1934
宗白華在《美學散步》有題為《中西畫法所表現的空間意識》,當中述及按照德國哲學家康德(Kant)的說法,人類空間意識為直觀先驗格式;當中又提到,根據德國學者舒尼達(Max Schneider)的研究所得,「音樂的聽賞裡也聽到空間境界,層層遠景」;而歌德(Johann Goethe)有此說法:「建築是冰凍住了的音樂」,由此可見「時間藝術的音樂和空間藝術的建築還有暗通之點」。
此場講座縱橫引述,當中提及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地理哲學」(geophilosophy)概念--他論及音樂、電影、繪畫的「皺褶」(folds),此後就在西方思潮掀起連場不現則、無定向、不斷越界的「皺褶」遊戲;另一法國作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認為,世人俱為性欲所罩上的禁忌,可又通過生命科學而打破此一禁忌;在巴塔耶看來,文學與藝術的本質,大概在於人性的惡之再現,所表現的正是此種動物性。
在講座中,觸及西方的立體主義繪畫--就從1900年至1910年的世界變革說起吧,其時汽車、飛機、無線電、摩天大樓等新興事物相繼湧現,物質世界遂爲藝術變革而搭建全新舞台,從普朗克(Max Planck)的「量子論」(quantum theory)乃至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狹義相對論」(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俱在1901年至1905年陸續誕生,視覺藝術觀看世界的方法有別於牛頓時代。
英國藝評家約翰伯格撰有《立體主義的時刻》(The Moment of Cubism)一文,詳述立體主義畫派誕生於1914年,在西歐一直持續至今的新型苦難:「人們在自身內部與事件、認同與希望的意義奮戰」,「盤繞在自我與世界新關係中的負面前景。人們所經歷的人生變成一場自我的內部混亂。他們迷失在自身內部」;「那個無論如何再也無法與他們切離開來的世界,在他們心中又回復成與他們分離且反對他們的那個舊世界」:所以立體主義畫家活在新舊的世界的夾縫之中,就好像已被迫將上帝、天堂及地獄俱全然吞下,就在內部與碎片永遠生活在遺棄的處境之中。
作者簡介:葉輝先生,資深書評家、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