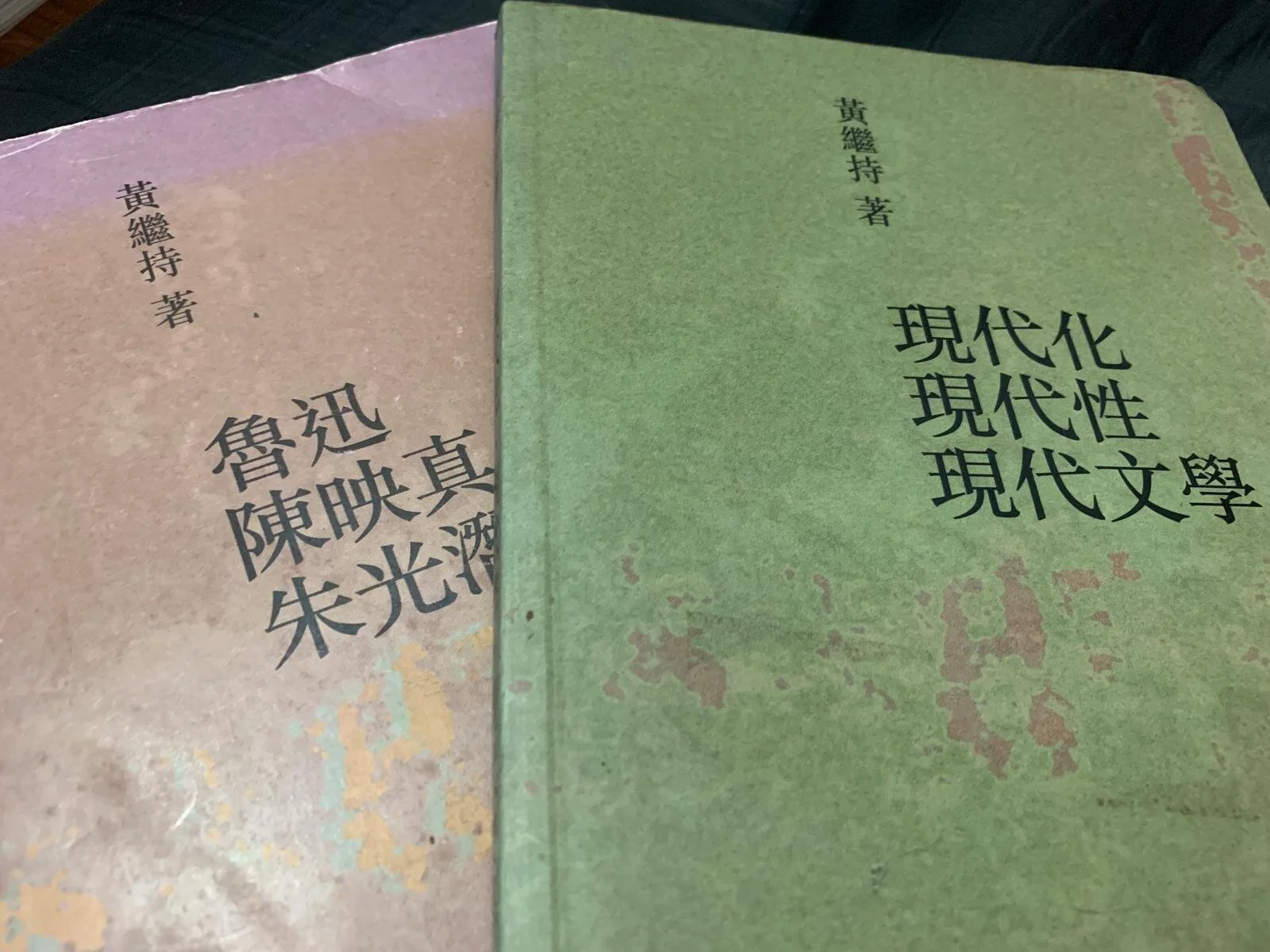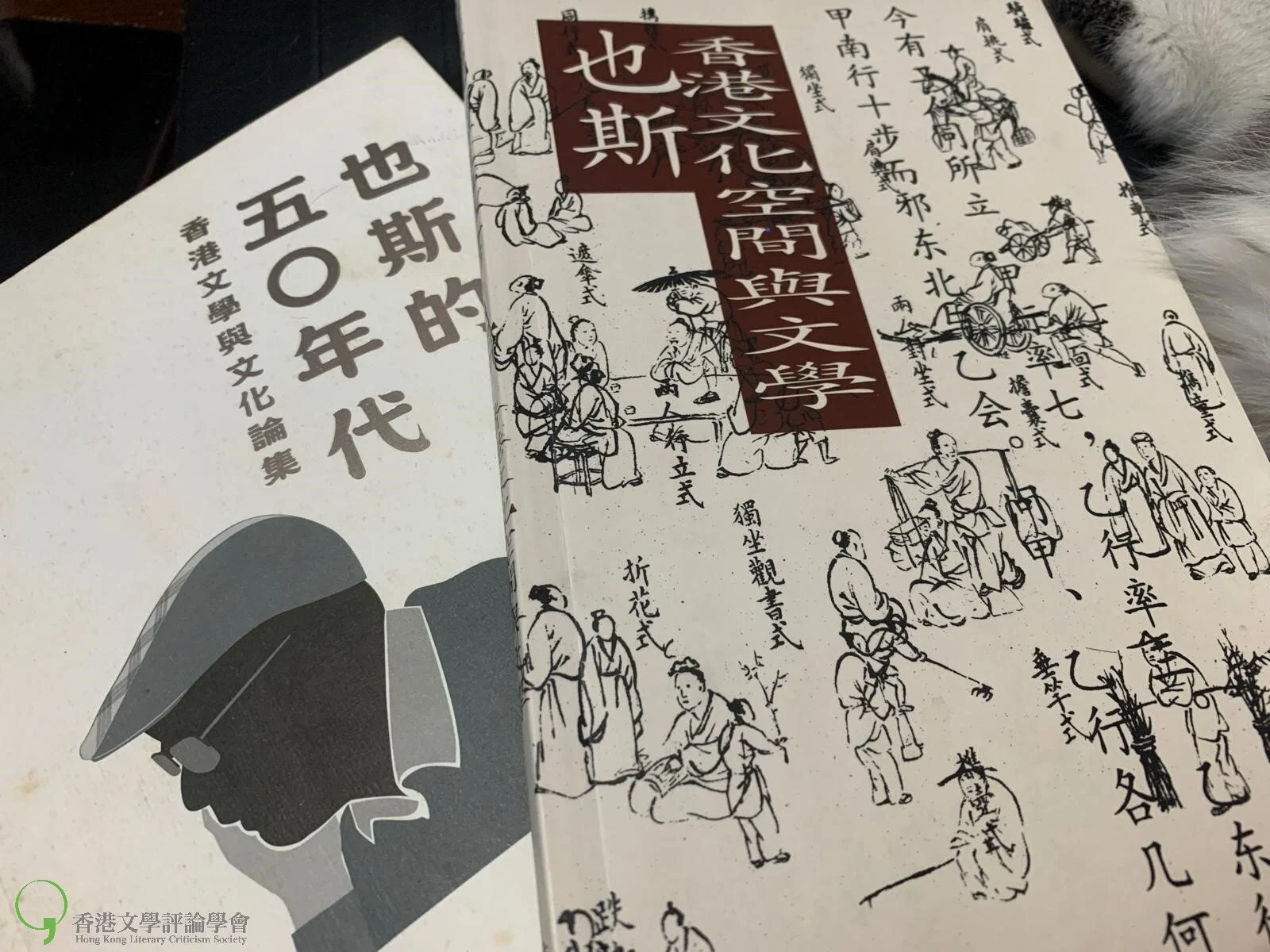文/張承禧
邵洵美(1906—1968)是新月派詩人,出身於官宦世家,曾留學英法,與徐志摩並稱詩壇雙璧。志摩成了詩人的代名詞,洵美卻被世人遺忘。邵與左翼作家不咬弦,曾被文壇巨擘魯迅惡言相向;邵的身份和作品有違1949年建政後的意識形態,晚年景況淒涼。即便80年代獲得「平反」,討論也不離他的情史,或簡單地標榜他為唯美主義詩人,卻不知其「唯美」風格沒有持續多久;他花了最大心力經營的兩項事業,出版和翻譯,常得不到重視;更為人忽略的是,邵是寫針砭時弊幽默文章的高手,更是民國其中一位最重要的文藝批評家。
陳子善在2005年為邵綃紅所撰《我的爸爸邵洵美》作序說:「他的評論集《火與肉》和《一個人的談話》,不要說至今未得到應有的評價,即使是專門的研究者,恐怕也有許多未曾聞見」。[1] 十多年過去後依然如是。陳子善認為〈一個人的談話〉[2] 「在邵洵美為數眾多的文學論述中佔有一個特殊的位置」、[3] 沈從文稱此文為「最美的散文詩」、[4] 邵謙稱它是「有連續性的備忘錄」,[5] 而筆者以為,它更像是一篇觀照自我的評論人手札。本文嘗試拋磚引玉,闡述文中的一些文藝觀,兼藉此反思五四新文學運動。
邵洵美
自我是從觀照中彰顯
〈一個人的談話〉所對應的,是兩個人或以上的談話,或一個人向眾人的談話。兩個人或以上的談話,是價值觀之間的交流,自會產生爭執和虛偽的理解,如邵於文中說:「最奇怪這世界上專多一般要求人了解的人,以及一般專要去了解人的人,於是便有分辯,誤會,爭論,怨恨,懊悔,種種的笑話。」[6] 小至日常爭吵,大至種種的主義和學說亦然。真正的理解是從自己與自己的談話而來。故此一個人的談話也不是演講或獨白,[7] 而是自說自話的觀照。正由於是一種觀照,真正的對話才會產生,由是構成這篇文章。標題用「一個人」代替「我」而拉開了距離,表明這並不是一篇甚麼文學家、甚麼派系的文藝宣言,而僅僅是「一個人」的供狀和觀察,也是邵接近而立之年,對自身文藝觀的回眸。恰如文中說,詩「是一種供狀,是一種觀察;而不是一種領悟,或是一種會心。」[8] 如果覺得文學是能夠領悟什麼的,離文學就遠了。
文學更加不是直線的表達自我。邵引用艾略特之說:「『詩不是去放任情感,而是去逃避情感;不是去表現人格,而是去逃避人格。』但是他又說,『祇有那種有人格有情感的人,才知道怎樣叫做去逃避那些東西。』」[9] 這與時人常以為詩是表達作家情感的說法恰恰相反,邵也借他人之口批評了一些只是浮淺情感宣洩的新詩。用佛家的說法,一旦有了「我執」,執著於「我」的在場、「我」的絕對性,「我」就會刻板化,反而遠離了真正的、誠實的「我」。換言之,文學最難能可貴的是,怎樣從「無我」中得見「我」。新文學誕生於「啟蒙」,亦盡受其約束。由引進「個人」一刻起,就帶來了「集體」,集體主義正是來自「我」的澎湃感情。就此來看,新文學作家所歌頌的「個人主義」與文學有著根本衝突。同樣地,如批評家僅以「個人主義」來定義五四作家,只會刻板化、庸俗地統合了該時代的作品,亦扼殺了該時代本有的文學聲音。
五四新文化運動
「定義」的專橫與文學學院化
新文學的興起掀起了甚麼是新詩的討論。然而邵直截了當地說:「我不喜歡定義,定義慣常是低能兒的工作。」[10] 意思就是,詩有著它應如是則如是的本色,是「創造」,[11] 並不需它者來定義,定義都是庸俗和遠離了詩。作品既是獨一無二的創造,又豈能經定義解釋?定義僅是為了遷就那些「看不懂」詩的俗人。他引艾略特的說法:「真的詩在未被人看懂以前即能點化」,[12] 一旦「看懂」,詩的神聖不再,即淪為俗物。這不代表刻意造出古怪語言就是詩,[13] 詩是「去洩露一種為平常人所從未領悟過的神秘」,[14] 類似於宗教的情感。這正是傳統批評最重視的不可言說傳統,「道可道,非常道」,是對「字」本身神聖(道)的尊重。這傳統已在理性之名下,屈從於學院的論文需求,經西方語言學拆解至體無完膚,因分科而變得支離破碎。
「定義」於今天成為顯學,作品總要用主義和思想去概括(或作者深受影響而預設了批評路徑),才能完成「學術成果」。文學趨於學院化,定義和理論分析駕馭了這門情感之學。邵說的「低能兒」不無諷刺意味:「所以我覺得假使一個人不想做詩學教授,他祇要能鑑賞一首好詩便成了」。[15] 今天,不單是批評家,連文學作家都要棲身於學院,作品儼如是對職位的「定義」,唯「俗人」只有圈內的孤芳自賞。「在中國,你要做一件事情,你非得同時做這件事情的教授不可。所以一個個寫文章的都會變成一個個說教者。」[16] 教研與創作本是最不匹配的組合,卻是現代「文學工作者」最常有的頭銜。當「定義」的權力愈來愈大,也是人愈來愈不尊重文學的純粹和神聖的時候,最後文學將變得無意義。〈一個人的談話〉珍貴的是,它道出一種新文學出現時的初心,非為服務「新文學」,而只是對文字、文學和情感的神聖敬仰。「牠有一種宗教的力量,牠會給我們一種生活的秩序。」[17] 文明的進步來自敬仰而非延異。
趣味抗衡庸俗,展現人格
然而如果作品變成絕對純粹、神聖、不可批評,就會變得封閉和極權,等於白白浪費了啟蒙思想。故此批評非常重要,但怎樣不落入思想的牢籠,就在於經驗、趣味和天才,這些都是融入於自身的東西。邵於文中提到,高尚趣味與庸俗對立;能從學究中培養,卻不是學究;更加不是道德、政治或宗教。它是真正個人領域上的立足處,如周作人說的「自己的園地」,它代表著一個人的天賦和經歷的累積。邵曾說艾略特「祇用歷史的方法去敘述每一個時代的詩人或批評家對於詩的見解」。[18] 從而避免對詩作出時代的專橫定義;同樣地,邵於文中寫了一大段文學經歷的自白,並說「對於自己趣味的表白才是一篇真正的供狀。」[19] 即是說,高尚趣味不是由上而下置入,而是逐步隨著一些天賦的東西、不知甚麼原因的安排、自然、感覺、隨興、機緣巧合、幻想、幽默等慢慢建立起來。〈一個人的談話〉侃侃而談,皆因見解都是經過作者的累積、消化、沉澱和重新提取,變成了自己的東西,形成文藝觀。舉重若輕,最難也是最容易。如此坦白、率性、一針見血的文章,今天已不多見。
郁達夫
邵評當時的作家:「魯迅有天才,沒有趣味;茅盾有趣味,沒有天才;達夫有天才又有趣味,在他的作品裏,我們可以看見他整個人格。」[20] 筆者以為,邵認為魯迅和茅盾的作品都是先有觀念,而不像郁達夫般直視自我,作品如供狀般反映自己的性情和欲望。魯迅和茅盾後來都刻板化為左翼戰士,其反抗之聲亦淪為政治宣傳。當代中國的問題,正是從「不見人格」開始。「高尚趣味是建設的,低級趣味是破壞的。」[21] 高尚趣味是人格和國體的建設,而低級趣味只會掩蓋人格和破壞美感。真正有趣味的人很少,天賦與機緣不可強求,但對一個國家或地方能夠展現國格卻是不可或缺,恰恰因為高尚趣味者不附和庸俗政權或立場。抗衡極權的,不是個人主義或革命,而是趣味。「高尚趣味也沒有道德觀念,因為牠不被社會的習俗來轉移。道德的標準是跟着時代變易的。」[22] 高尚趣味的人能看穿由上而下觀念的置入、時代道德的可笑,並透過自身經歷、對文學和歷史的尊重,展示出真誠的自我和人格。一個社會的文化格調就建立起來。
定義「新文化」的自信催生文化革命
新文化運動最大的發見是「自我」,同時也是最大的桎梏。文學和天馬行空的想像,都加上了個人主義、政治啟蒙、自由價值等的包袱。謂之「解放」,卻是專制的「八不主義」;[23] 非寫某種文字、主題、文類不可。受盡今人批評的左翼文藝,與被稱譽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並無二致。從這些「進步」價值中誕生的新文學本身就是問題。30年代小品文興起,周作人將之上溯晚明小品,可說是對西方進步價值和「自我」發現的一種消退和回歸。
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一個人的談話〉有意思的是,邵不是從「我」,而是從觀照自我的角度出發去談文論藝,亦即他說的「供狀」。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何他突然於文中插入一個西洋故事、一部劇作的想法、羅列自己的文學經歷,因為這些都是「供狀」的一部分,類似於自己對自己的審視。這些審視消解了「自我」的「定義」,故此詩是逃避情感、小說是作者進入書中世界、文章是一個人的談話。自始,批評便不僅僅是對作品的批評,而同時是對自身的批評和創造。如是者,批評便不是為了什麼觀念而寫,而能自成「作品」。這種觀照自我的文藝觀也見於他的詩作上,如〈你以為我是什麼人〉:
你以為我是什麼人?是個浪子,是個財迷,是個書生,是個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錯了,你全錯了;我是個天生的詩人。[24]
這是一位傳奇詩人透過詰問來確立自我的一份供狀。它被銘刻於邵的墓上,象徵詩人與詩的永恆對話。
這種拉開與「自我」距離的做法,在極端自信(同時極端自卑)的五四新文化中尤顯珍貴。新文化運動以「新」為號召,「我」要與一切「舊」的切割,「我」的當刻便是「新」和最好,把線性的科學發展觀、革命觀引進了文學。須知史上成功的文化運動,如文藝復興、古文運動,皆是以復興上古傳統為號召,而鮮有自命為「新」。新文化運動後,極端自信帶來的就是極端理性與瘋狂、極美與極醜,失卻敬畏心。真正的啟蒙帶來的不是人的全知,而是人的渺小和無知。這是觀照自我的重要。
[1] 陳子善:〈序〉,《我的爸爸邵洵美》(邵綃紅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2。
[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人言周刊》,第1卷第12期至第27期(1934年5月5日至8月18日)。
[3] 陳子善:〈編選者言〉,《洵美文存》(邵洵美著,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6),頁3。
[4] 邵綃紅:《我的爸爸邵洵美》,頁137。
[5]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上海:第一出版社,1935),頁3。
[6]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7。
[7]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3-4。
[8]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4。
[9]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36。
[10]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4。
[11]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5。
[1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1。
[13]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2。
[14]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25。
[15]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8。
[16]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1。
[17]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5。
[18]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15-16。
[19]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60。
[20]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63。
[21]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6。
[22] 邵洵美:《一個人的談話》,頁56。
[23]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正文起頁21。
[24] 邵洵美:《詩二十五首》(上海:時代圖書公司,1936),頁36。
作者簡介:張承禧,嶺南大學中文文學碩士。現於出版社工作,研究興趣為香港文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評論曾收入《本土、邊緣與他者》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