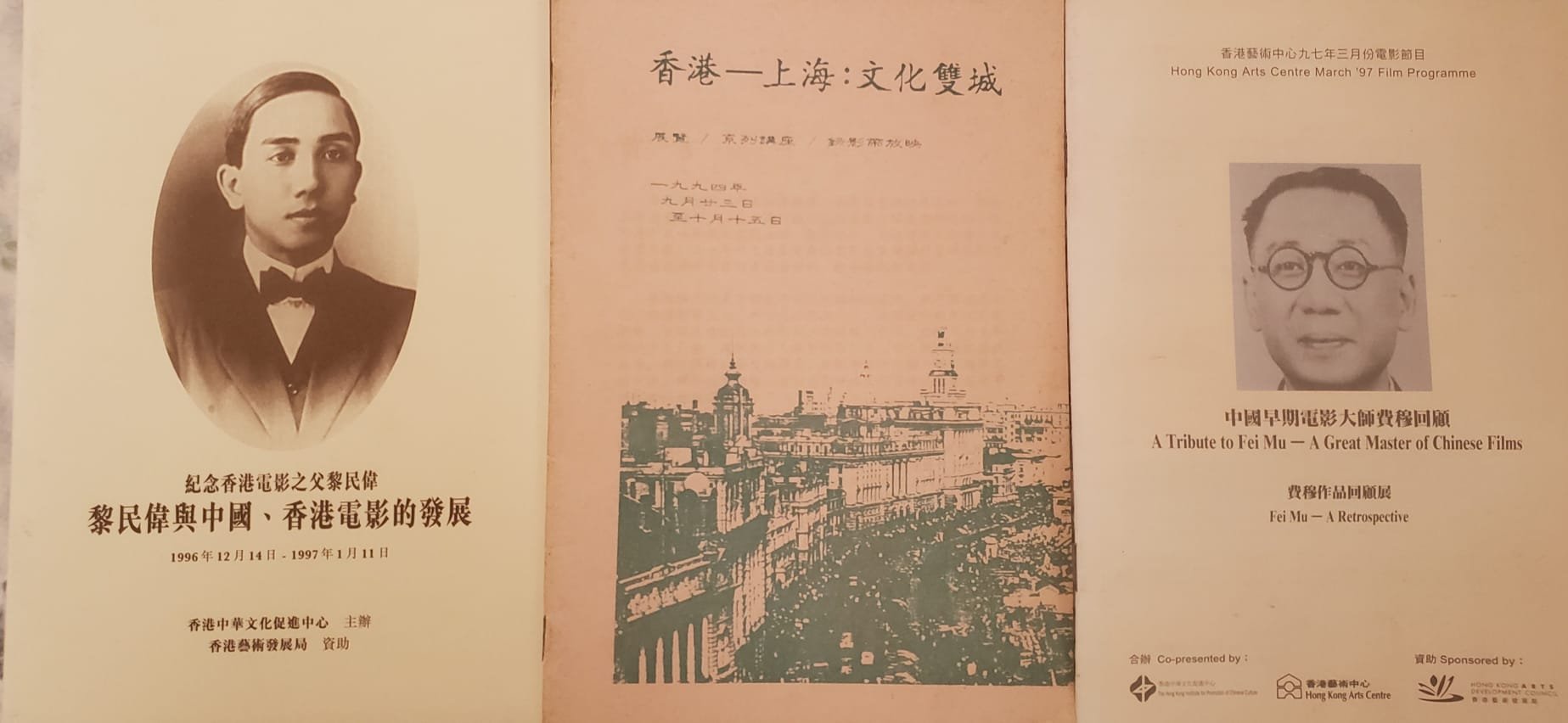人們往往將〈魚之雕塑〉這篇小說與1950年代開始的難民潮掛勾,認為這是西西是在寫那個時代的偷渡客處境、反映現實問題等便不再深究。然而,筆者認為〈魚之雕塑〉不僅僅反映現實問題,更是透過敍事手法,將「藝術需否接受者了解創作背景」這一主題呈現出來。
文/魏諾晴
〈魚之雕塑〉是西西於1981年寫的短篇小說,收錄於短篇小說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西西的作品常常以疏離的角度描寫社會,例如《我城》寫70年代的香港人,但〈魚之雕塑〉卻將有所改變,探討的是「藝術接受」這種更普遍的現象。「藝術接受」這一命題在香港這個「文化沙漠」往往是作家更直觀地面對的課題,作品評價很大程度受限於讀者的水平。但筆者發現人們往往將〈魚之雕塑〉這篇小說與1950年代開始的難民潮掛勾,認為這是西西是在寫那個時代的偷渡客處境、反映現實問題等便不再深究。然而,筆者認為〈魚之雕塑〉不僅僅反映現實問題,更是透過敍事手法,將「藝術需否接受者了解創作背景」這一主題呈現出來。
〈魚之雕塑〉是西西於1981年寫的短篇小說,收錄於短篇小說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西西在〈魚之雕塑〉中主要用了兩種敍事語言來寫這篇小說,分別是「我」與「他」對話時的日常化語言以及在描寫魚的雕塑時的文學語言,(註1)而西西正正運用了這兩種語言來將歐洲美術館的畫作、雕塑與「我」沿着海岸散步時所看到的「雕塑」作對比,突顯出觀賞者對藝術品的感受與其是否充份了解作品的創作背景有密切的關係。西西以簡單而零碎的對話來描寫歐洲的名畫、雕塑,例如「原來有普通長餐桌那麼闊大,而且,顏色要比一般畫冊上的清麗明亮」(註2),寫秀拉的《海浴》時,是寫畫的尺寸、畫作所用的手法,寫《春天》和《維納斯的誕生》時是寫畫面上的金色與畫冊上的印刷品的差異、寫畫面上的溫度計顯示畫作是在甚麼時侯畫的。這些都是細碎的、顯淺的,不是以畫的整體來細緻的描寫,而是粗淺的帶過。整段是以對話體、用日常化的語言呈現,為後文「我」和「他」在海邊看到魚之雕塑時的反應作鋪墊。
在看到魚之雕塑時,描寫卻是這樣的「我們走得更接近,才看見兩隻展敞在軀體左右僵硬無力的手,裸露在袖管的末端。雙手都剩下半個手掌,因為所有的指節,如今都變成光滑的灰白骨頭」(註3)。敍事語言由人物的日常語言切換到隱晦的文學語言,把本應醜陋雜亂的屍骨寫得極有刻意創作的美感,使那些聞名天下的名畫、雕塑在文本上的重要性上比這具由無名的藝術家(魚)所造的雕塑(屍體)較低,將後者寫得更優越,兩者之間產生鮮明對比,塑造出巴赫金在《狂歡化詩學》中提及的嘲弄權威作用。(註4)放在歐洲著名美術館的名畫、著名的雕塑理應是高高在上的,但在西西的筆下卻描寫得不如魚吃剩的屍體詳細、重要,這樣的描寫將這些名畫、雕塑與岸邊的屍體的地位顛倒了,甚至不寫常人該有的震驚,反而顛倒成為觀賞藝術品時的「冷靜」,從而產生陌生化的作用,對凸顯小說主題有所幫助。
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1895年11月17日-1975年3月7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проблемы поэтики достзевского)談論狂歡化的問題。
沒有共鳴的背景而使人難以感動是小說的主題。歐洲的名畫反映的是數十、數百年前的生活,但魚之雕塑不一樣,「我」和「他」都生於那個時代背景,正切身處地經歷難民潮,能夠想像那一具浮屍抱着何種心態在海上奮力游來香港,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被魚、被自然吞噬。因此才使「我」和「他」都格外震驚。兩者的差異正是如此:因為作為接收者的人並不了解那些名畫、名雕塑的創作背景,失去這些背景支撐使得他們只能零零碎碎地說出膚淺的感想,而當他們看到一件似是與他們休戚相關、貼近生活的藝術品,由於作品與他們的世界那麼的接近,便會產生深刻的評價。這就是造成評價差異的原因,而非藝術品本身的能力所影響。而這篇小說也是一樣,如果不了解寫作背景便無從得知「我」和「他」為什麼會如此的震驚、感動。
近日,西西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終身成就獎。
筆者認為西西正是想透過差異較大的日常化語言與文學語言的混用來將兩者的地位顛倒、陌生化,從而表達出藝術的接收者對作品背景的理解使得他們對一件作品的評價有所差異,表達了解創作背景、作者所發映的真實生活對接受作品之重要性。
註1:劉來春:〈論文學語言的陌生化〉,《雲夢學刊》(2004年3月),頁107。
註2: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7。
註3: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60。
註4:夏忠憲:《巴赫金狂歡化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96-97。
作者簡介:魏諾晴,香港專上學院文科副學士。自中學時便偶爾寫作,喜歡卡謬、費茲傑羅等作家。除了文學以外對其他藝術如電影、表現藝術等都頗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