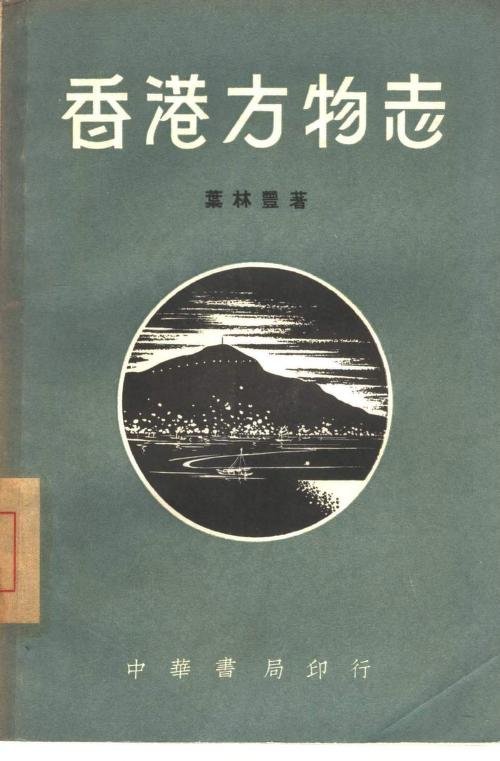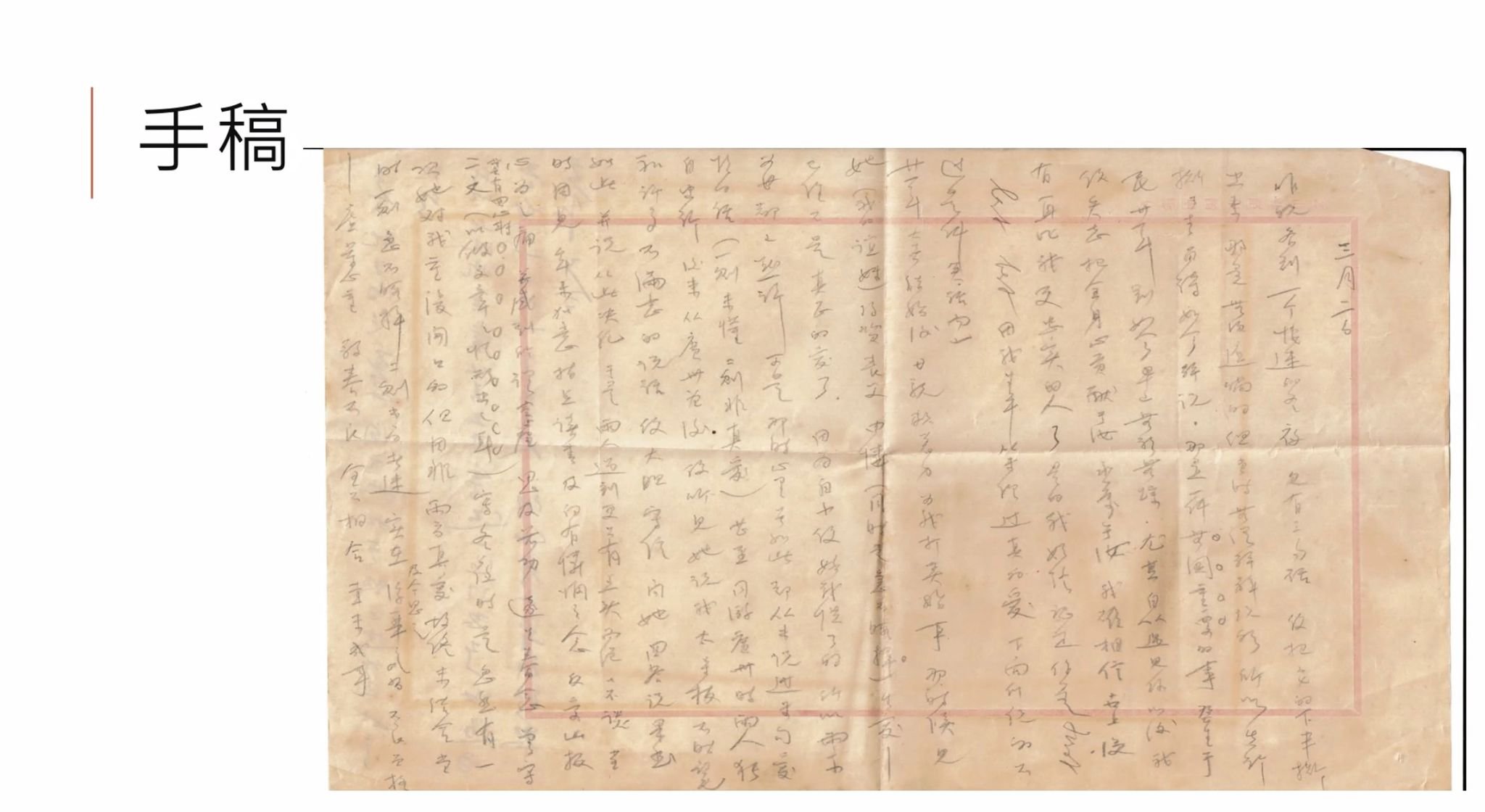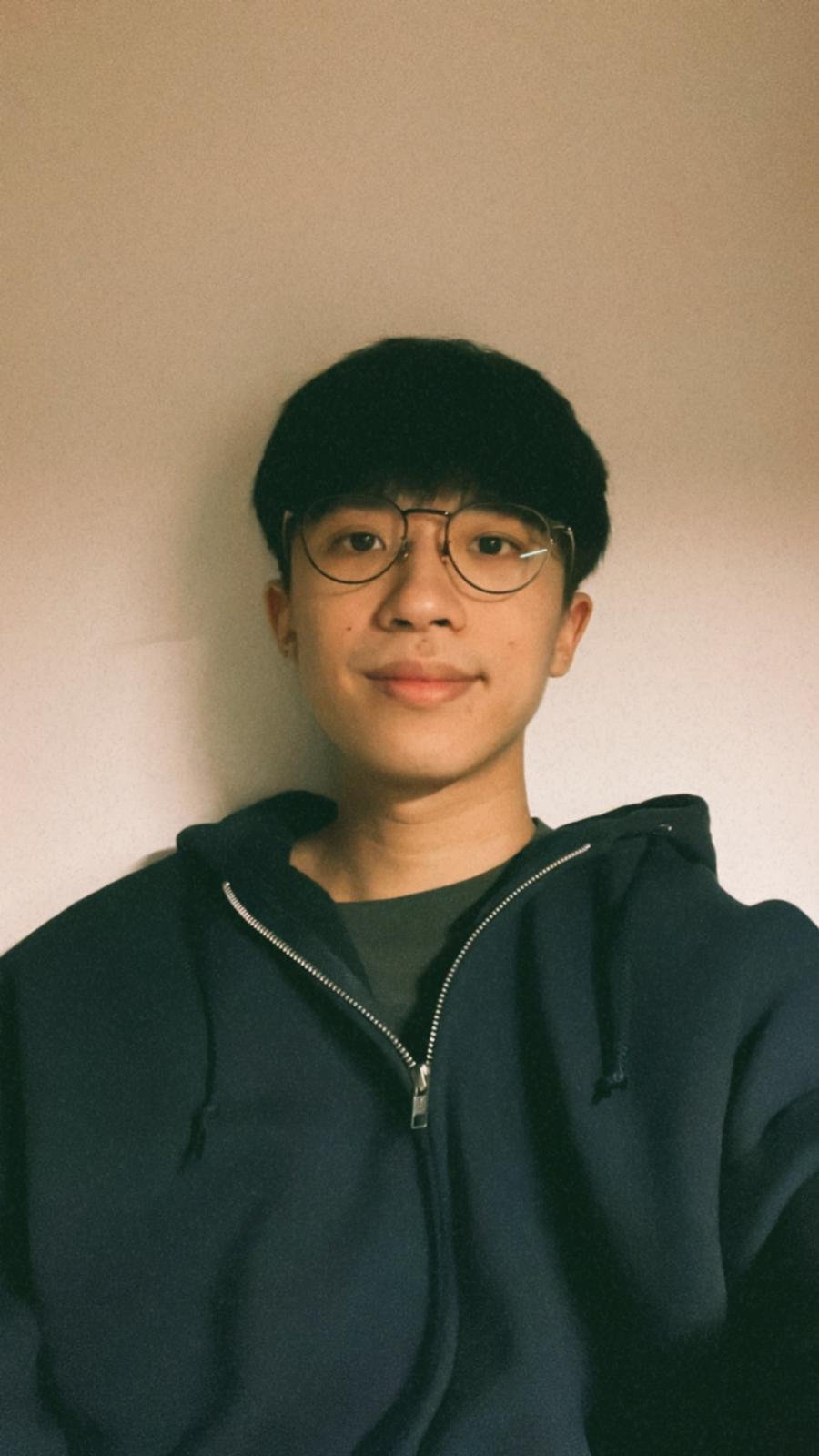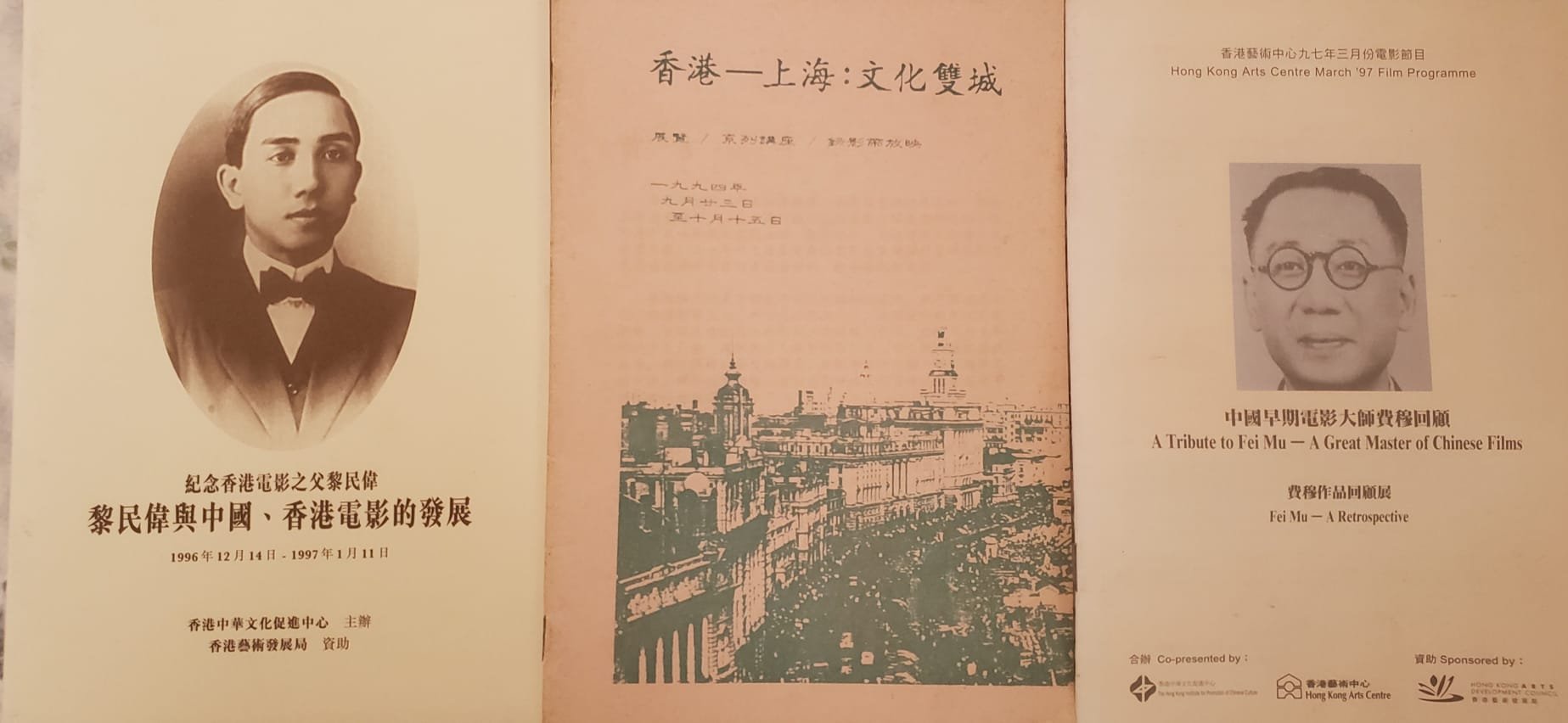《隱山之人In situ》在書寫破碎和救贖,我們在躁動的都市中尋求安定,人類自詡萬物之靈,久而久之,便忘卻了我們和動植物最根本的相似之處。我們其實是受傷的幼獸,也是無處落根的植株,唯有在大自然的包容下,我們的靈魂才能得到平靜。
文/許雅如
《隱山之人In situ》無法被輕易定義,它可以是一本香港生態圖鑑,是一份給人類的起訴狀,又或是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而我認爲,它在寫香港人的生存困境。城市的喧鬧使我們的靈魂沾上塵埃,連肉身也變成累贅,一切慢慢分崩離析,面對破碎與殘缺,我們轉而向大自然尋求救贖。
作者以植物喻人,夏花是脆弱、短暫的草本植物,方宗柏是堅韌、長青的木本植物。但無論柔弱如夏花,或強壯如柏樹,都無法適應混凝土夾縫中的生活,要阻止消亡,他們必須向高處移動,尋找得以植根的地方。山路崎嶇,爬山如同行走在人生的重巒曡嶂上,中途或有霧,或有雨。夏花患有人格解離障礙,與丈夫分居;方宗柏被城市的急速節奏壓迫,家人不在身邊,師傅去世。他們都被迷霧和泥濘掩蓋,夏花無法看清自己的存在,方宗柏沒有能夠停駐休息的家,於是孤獨迷茫的二人遷移至山上,等待靈的指引。
故事以「我」的視角展開,以「你」指代方宗柏。作者並沒有直接説明「我」的身份,「我」有可能是長居山中的神祗,或者是偶然游蕩至此的鬼魂,隨著時間推移,「我」早已和大自然融為一體,成為這個山中的靈。第二人稱使讀者從大自然的角度俯視眾生,感受她對萬物的包容。夏花和方宗柏不屬於這個秘境,就像方宗柏所説,他們是「外來入侵種」,夏花不小心踩死尖舌浮蛙,方宗柏把烏桕大蠶蛾做成標本,他們的到來侵擾了本來靜謐的山林。面對二人的行爲,以及山下人類活動的傳聞,山的靈在旁邊看着、聽着,從祂的語氣中沒有感受到憤怒,只有平靜的敘述。這種包容不僅是不批評,而是對事物存在的承認和接納,捕獵與被捕,狂風與暴雨,連同二人都被一一收納在大自然的生命迴圈中。
《隱山之人In situ》的作者葉曉文,一直關心香港的自然生態,例如著有《尋花2-香港原生植物手札》,繪錄香港原生植物品種。
在山中,所有靈魂都是對等的,夏花和方宗柏都能夠接受大自然的饋贈。石屋後的小水潭除了供給二人的日常用水,還有洗淨靈魂的作用,它為夏花拭去滿身泥濘,讓她在每日清晨的浸洗中修補靈魂。山中的靈比方宗柏更早洞察到夏花的情緒,當夏花捲縮在岩石和大樹上,試圖將俗世的記憶和悲傷都沉降在大地之下,大自然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一切。在如此神聖和包容的大自然裏,夏花和方宗柏仿佛褪去了皮,僅以靈魂的形態存於山中,兩個純粹的靈魂產生碰撞,得以相遇和相愛。方宗柏不再孤獨,夏花的求救得到回應,二人互為對方的伴生植物,在山中生根發芽,成爲了生態系統的其中一環。
故事的結尾,迷霧再次襲來,夏花需要獨自面對困難與險境,而方宗柏被困於無法幫助夏花的無力感中。值得慶幸的是,夏花展現出了堅定的意志,就好像石龍子面對死亡時斷尾求生的魄力一樣。作者並沒有告訴讀者二人的結局,但我相信只要他們把自己交託給大自然,就能夠找到一線生機。
《隱山之人In situ》在書寫破碎和救贖,我們在躁動的都市中尋求安定,人類自詡萬物之靈,久而久之,便忘卻了我們和動植物最根本的相似之處。我們其實是受傷的幼獸,也是無處落根的植株,唯有在大自然的包容下,我們的靈魂才能得到平靜。
作者簡介:許雅如,文學新鮮人,就讀於香港專上學院,來年準備升入大學。雨天、動物、大自然,是我寫作的靈感來源。假如憂鬱無法排解,就去擁抱它,它可能會是文學路上一個不錯的旅伴。